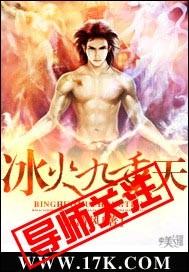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裁判有问题 > 第17章(第1页)
第17章(第1页)
&ldo;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可没有干涉你,不是吗?&rdo;
&ldo;对,你仅仅是把我最好的词句都删掉了嘛。&rdo;小说评论员慢慢踱过整个房间,来到编辑身后,看着编辑正在删改的拷贝,发出一声绝望、被刺痛的哀号,&ldo;老天,你没删掉那段吧?不过,我的老天,这是为什么?那又不是出言莽撞,那只不过是说……&rdo;
&ldo;听着,陶德杭特,柏雷是这样写的:这本书充斥着空洞的词句,犹如成团堆积的凝同奶油,如果这是费金先生的第一本书还有情可原,因为这只说明他认为没有必要在使用一种工具之前了解其用法,然而这已经是他的第六次尝试了,在此之前,他起码应该学好英语语法。但是,这已经是他的第六本小说了,至于在冗长的赘言底下,是否还隐藏着什么深意,这我可看不出来。费金先生那种滔滔不绝、毫无意义增长句子的能力,固然赢得我不少同事的赞誉,这让他的早期作品颇受好评,但或许这次他们应该解释他是如何写出这本书来的。抑或,这是个只有出版费金先生著作的人才知道的秘密?柏雷居然还敢说,这并不是出言莽撞。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rdo;
陶德杭特先生露出不以为然甚至略带内疚的微笑说道:
&ldo;或许这样说是有点太坦率了。&rdo;
&ldo;简直太露骨了嘛。&rdo;费瑞斯大加附和,并在这段令人不快的文字上,大笔一挥,打上两个大叉叉。
这名饱含激情的评论员愤怒地跺着脚来回踱步,说:
&ldo;我真看错你了,该死,陶德杭特,你应该支持我的。当然坦率,干吗不能仗义执言?也该有人出来批评一下费金了吧?这家伙被捧上天了,简直荒谬。他根本没写出什么好作品,该死的家伙,简直可以说是烂透了!他之所以得到这些令人作呕的赞美,是因为有些评论者根本懒得花费心思看他的文章,所以认为空洞的表扬应该比批评更容易;另外一些评论者则真的认为这种无法无天的长句子,是某种天才的表征,面对精练简洁的文字,这种评论者就是无动于衷。也可能,他们知道大众喜欢钱花得有所价值,但他们误解了大众的喜好,认为冗长就代表了价值。该死,这种幻影到该幻灭的时候了,不是吗?&rdo;
&ldo;你说得很对,小伙子,&rdo;费瑞斯回道,面对评论员爆发出感情,他显得相当镇静,&ldo;不过,杀鸡焉用牛刀,毕竟,用屠刀戳泡泡可真没意思。如果我让这篇文字见诸报端,隔天上午就会收到十几封来自老淑女们的信,她们指责我们如此攻击费金先生辛苦写出的书,实在有失公平;况且他人畜无伤,难道我不能找一名没有私心的评论员来写吗?&rdo;
&ldo;我可没有任何私心!&rdo;评论家口沫横飞地怒吼。
&ldo;我知道,&rdo;费瑞斯安抚道,&ldo;但她们不知道呀。&rdo;
陶德杭特先生随意从书架上挑了一本书,然后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间。当他离开时,他还听到后头柏雷先生激昂的讲演:
&ldo;很好,我不干了。这些可恶的老女人,我才不在乎她们。你要是不让我按照自己想法写文章,我就辞职。&rdo;
陶德杭特先生知道此事并不必放在心上,在每个星期三下午,要是柏雷先生凑巧看到他文稿被删改的情形,总是威胁要辞职;如果没看到,他就会忘记自己写过什么,然后保持一颗愉快的心。无论如何,只要费瑞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跟他说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无法找到另一个符合《伦敦评论》水准的评论家,柏雷先生的情绪一定会软化下来,并同意再多留一星期。这样的情节总是周而复始地发生。
当一名文学编辑最重要的是老练。而第二与第三重要的,还是老练。
陶德杭特先生异常狡猾地暗中开始行动。
他希望多收集一些关于欧吉维亚被革职的信息,虽然费瑞斯不愿告诉他,但陶德杭特先生知道从哪儿可以打听到一些小道消息,于是也走向助理编辑的办公室。莱斯里&iddot;威尔逊是个交友甚广的年轻人,有他自己的一番文学抱负。他和音乐编辑分享一间办公室,但是后者却很少出现。陶德杭特先生邀请他去楼顶餐厅喝茶,威尔逊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除了费瑞斯和编辑主任外,令年轻的成尔逊深感敬重的人为数不多,然而陶德杭特先生细腻拘谨的举止与学究式缜密的思维,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青年面前,陶德杭特先生也略感惶恐,要是陶德杭特先生知道对方对自己怀有好感,准会大吃一惊。两人搭电梯上楼,陶德杭特先生骨瘦如柴的身躯靠在一张硬邦邦的椅子上,然后沉稳地向女服务生点了中国茶,并往茶壶中加了很多匙茶叶。威尔逊毫不掩饰自己喜欢享受美食茶点这一爱好,这点和陶德杭特先生的饮食观恰好相同。接下来,他们用八分钟讨论书籍。在讨论结束之前,他把话题引到了欧吉维亚,看到威尔逊激烈的反应,他感到非常高兴。
&ldo;真是丢人现眼!&rdo;年轻的威尔逊愤慨激昂地说道。
&ldo;是啊,为什么会突然解雇他呢?&rdo;陶德杭特先生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倒了一杯茶,然后把糖罐送到客人的面前。这个时候吃下午茶还早,餐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ldo;我一直觉得他是写文章的一把好手。&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