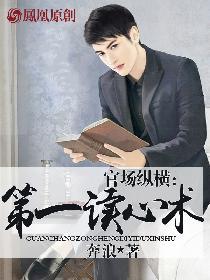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朋友妻逝世的悼念词 > 第23章(第1页)
第23章(第1页)
雨珠顺着发丝流进眼中,酸涩胀痛。
这就是她的十五岁生辰,饿着肚子,浑身湿透。
丝丝缕缕的伤感像裹在身上的湿衣裳一样,冰冰凉凉,虽不刺骨,却黏湿得难受。
一声惊雷似在耳边炸响,电光从黑云间劈下来,吓得陈茗儿脊梁一弓,心似被人捏着手里狠狠地攥了两把,方才涌上心头的那点顾影自怜的伤感瞬间就被惊惧驱散了。
陈茗儿慌忙捂住耳朵,又往亭中心挪了挪。
这个时候,她不可避免地想到了沈则,只是这个名字刚冒出来,陈茗儿就狠狠咬了下自己的嘴唇,算是对自己的警告。她不能允许自己再像从前那样,只等着别人来打捞。
脚下积水越来越多,鞋底整个浸在了水中。陈茗儿将脚收回在小石墩上,抱膝缩成一团,整个人竟也能安安稳稳地栖在小小的石墩上。
她将下巴抵在膝头,焦灼又无助地盯着将自己围困的暴雨。
雷声渐小渐疏,雨势却丝毫未见收敛。要不是顾及从疏影阁带出来的那些布料,她真想冒雨跑回去,她实在是饿了,肚子一直咕咕地叫个不停。
陈茗儿轻轻地揉了揉饿得有些发疼的肚子,动作间不经意地往身后掠了一眼,浑身的汗毛噌得就竖了起来。
两条野狗不知什么时候钻进了亭子里,就卧在陈茗儿的身后,此刻正虎视眈眈地看着她。
人在极害怕的时候,是连害怕都忘了的。
陈茗儿抠着石桌凹凸不平的边缘,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可浑身却不停地使唤地过筛一般发抖。
“不能跑,不能跑……用石头丢……”
她哆嗦着看了看四周,哪怕是个小石子她都够不着,陈茗儿刚要尝试着伸脚去拨,野狗对着她警告似都急吠两声,惊得陈茗儿差点从石墩上摔下来。
她猛地想起头上的发簪,一把拽下来,握在手里。
两条野狗却没吓到。反倒向前走了两步,嘴边的黏液扯得老长,露出尖尖的獠牙。
陈茗儿扶着石桌慢慢地站起来,攥着发簪的手心里全是冷汗。
野狗抢食为生,凶残似狼,凭着陈茗儿这点微末力气,是逃不过的。
她心里清楚。
她一点点,一点点地,以几不可见的距离往后退,对面的野狗却似耐心耗尽,伏在地上,粗重又不耐地哮着,爪子在泥泞中拉出骇人的痕迹。
陈茗儿膝盖一扣,人眼看着要跌坐在水滩里,突然被人扶住了后腰,稳住了。
“你胆子够大的。”
沈则一只手顶着陈茗儿的背,腾出另一只手将短刀脱鞘。
看清来人,陈茗儿眼眶一红,是半点力气也没有了,手指死死地拽住沈则的衣袖,整个人挂在了他身上。
姑娘娇软的身体就毫无防备地贴上来,沈则呼吸一凛,手掌扶着她的腰,不敢用劲也不敢不用劲。
陈茗儿此刻哪还顾得上这些,指着他手里不足小臂长的短刀,眼泪都快下来:“行……行吗?”
人软成这样,竟然还顾得上关心这把刀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