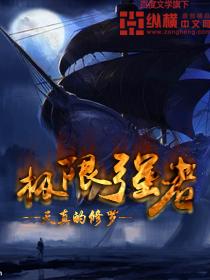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东京旧梦by江湖一支笔有下么 > 第47章(第1页)
第47章(第1页)
“姐姐……”
“你别过来。”女使和仆役就在不远处的庭院中,只要张清涵稍一呼喊,就能让他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化为泡影。
但张清涵却没有这么做,她只是惊疑不定地看着面前的男人。直觉告诉她,面前这个人身上还有一丝她熟悉的味道。
男子注意到她隐在信笺下的手掌中还悄悄攥紧了一枚银钗,有些无奈地看向了这位外柔内刚的女子。
他先向后退了一步,表示自己不会对她不利,复收起了故作的温柔换了副口气道,“那首词是当初我咄使他填的,否则就凭张子初那个榆木脑袋,怎么可能主动写这种东西。”
那口气中,六分自若三分不羁,还夹着一分顽劣。
银钗落地,发出一声清脆的撞击。张清涵不可置信地捂着嘴巴紧盯着面前容貌可怖的男子,一直不曾涌出的泪水此时如同洪口决堤,一发不可收拾。
“希泽?你果真是希泽?”张清涵上前两步,一把拧住了对方的胳臂。
是了,若非那个小混蛋,又有谁能将“张子初”扮演的入木三分,差点连她也骗过去;若非那个小混蛋,又怎能一句藏头诗糊弄走了李秀云,还将自己逼得如此失态?
王希泽张开双臂,安抚着扑在他怀中又哭又笑的张清涵。偶尔路过两个女使厮儿大约是没见过自家娘子这般模样,有些好奇地朝这里频频张望。好在他们只会认为,刚刚是因为李秀云在场,张清涵才勉强忍住了情绪。
“嘘,姐姐莫要害我,我可是九死一生才换到‘张子初’这身份的。”王希泽的手掌一下一下轻拍在张清涵背上,就如同小时候他受了委屈,对方护他那般。
待二人重新步入书房,掩上了房门,张清涵的情绪才稍稍平复一些。
“这么说来,子初已经被你偷偷送出城了?”张清涵安静地听他说完了金明池里发生的事,一时有些恍惚。
“我倒也有想过杀人灭口,不过希吟他心软,舍不得。”王希泽坐在案旁,托着下巴冲她比划了一个咔嚓的动作。
张清涵没好气地瞪了一眼,这么大的事,从他嘴巴里说出来仿佛儿戏一般,倒还有闲情同她开起了玩笑。
“你要这个身份究竟想做什么?”张清涵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果然见片刻前还表情促狭的人一瞬间沉默了下去。
“不能告诉我?”张清涵心中隐隐有一些猜测,但她不敢深想。按照这种情况来看,对方要做的事一定非同小可。先是勾结辽人,意图行刺,后是偷梁换柱,欲意欺君,光是这两点,就已经范下了滔天罪行。
“你不会是想替你大哥他……”
“姐姐。”王希泽快速打断了她的话,“我此番要做之事牵连甚广,绝不愿你也干涉其中。我看再过几日,你还是回庵里去吧,或者你想见子初的话,我也可替你安排。”
“我不走。”熟料张清涵却是一口回绝了他的提议,“你休想像对付子初那般将我弄出城外,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汴梁城中。”
“姐姐……你这又是何必。”王希泽见她神色决绝,知道怕是硬来不了的,只得周旋道,“你难道真不担心你弟弟?他这番可也遭了不少罪。”
张清涵微微一笑,莲步轻移走到了他身旁,“自然是担心的,所以才更不能走。因为我最担心的两个弟弟,不正在汴梁城中吗?”
“……”
“你不必告诉我你们想要做什么,但无论你们做了什么,我都会留在这里,陪你们一同承担……”张清涵说着,用双手轻轻捧起了他的脸颊,“一定很痛吧。傻孩子,你怎么对自己下得了这般狠手。”
女子柔软的掌心让王希泽心中某个地方也跟着柔软了下来。他选择闭上了双眼,短暂贪恋着这位姐姐的疼惜。
绝不能让她留在城里。
自己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会如同高空走丝,稍有不慎,下场就是粉身碎骨。罢了,再找机会吧,在真正的计划开始之前,一定还有机会将她哄骗出城的。
☆、风诡云谲仕途路
杏案前,一缕残烛摇曳。
重新关上的书房内,清瘦的人影正伏在案上,比照着一旁的画稿,一笔一划地描摹出几幅山水图。墨染生香间,正欲勒出些岩松,复又拿起手来吹了吹,瞧了瞧,似是觉得不满意,眉头一皱,整张脸上的疤痕更显狰狞。
随手揉了那纸,又取了一张来摹。
忽然,一旁屏风后伸出一只修长的手掌,虽是指骨分明,却也伤茧尤多,手一低,将地上的纸团捡了起来。
“明明已经很像了,何苦这么为难自己?”鬼魅而来的青年指尖一碾,将手中的纸团丢入了案旁灯烛的火舌中,使之瞬间化作了灰烬。
见案上的人不应他,青年缓缓走了过去,俯下身子去瞧对方的面容,啧啧叹息道,“可惜啊,那样好的一张脸,就被你这么给毁了。”
“你有空在这里废话,倒不如回去看紧那张正道。”王希泽终是抬起眼来,瞥了眼面前的沈常乐,一尺子捣开了对方撑在案上的手肘。
“你俩倒是有默契,我那日正巧听见马素素问他名姓,你猜他怎么说?”
“他也说他叫张正道。”沈常乐的话让案桌上的人笔尖一顿,微微勾起了嘴角。
“难为他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