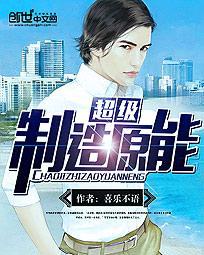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东京旧城 > 第65章(第1页)
第65章(第1页)
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一缕线索,张浚也不会放过。
金明池刺圣之事表面上看起来再简单不过,是辽人心生怨愤想要报复大宋。可若是细细揣摩,这里头的名堂可就多了。
例如,吕柏水为何会蠢到私保辽人入关?杨季又是怎么知道这事从而举发吕柏水的?杨家被鸩是何人所为?又是谁透露了李秀云临桥献瑞的风声,让辽人制定出了这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几个契丹蛮族,竟然连李秀云的行踪都摸得一清二楚,还懂得利用龙团胜雪这种东西来藏匿杀器。金明池这盘棋布得太过精妙,所以才越发显得蹊跷。
但最蹊跷的,还要属那个带着马素素一起消失在池中的男人。这个人先在角楼上打晕了一队建安卫,扒走了他们的胄甲;后在船舱中助李秀云偷梁换柱,逃出生天;最后却又扮作茶博士跟上了栈桥,打晕了礼部侍郎严信,救走了马素素。
此人行为前后矛盾,如同儿戏,一时难以判断是敌非友。他背叛辽人究竟是临时起意还是早有预谋?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张浚知道,萦绕在自己的面前是一团团浓雾。但他并不因此觉得为难,反而有些兴奋。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只要他一层层拨开这些云雾,背后的真相将会让天下人为之震惊。
而且,这个面相过柔的年轻官员,现在手中已经掌握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线索。
清平司后的这屋子是背阳而建,光线十分昏暗。张浚小心剔亮了屋里的灯烛,四面墙壁上挂着的大小画作这才一下子清晰起来。
张浚走到了屋子中央,那张硕大的大理石案桌旁,从桌上端起了两幅人像。两张画像上画着的都是一个青年男子,乍一看有些像,麻子脸,面色蜡黄。可若仔细分辨,却又发现不尽相同。左边那张里的人五官偏普通,好似随处可见,拿到大街上比照怕是一抓一大把。右边的则极富特点,虽是面色不济,但眉眼间却透着一股英气。
左边的人像是范晏兮从张府中拿来的,据说是张子初比照着严信二人的叙述画出的。而右边那幅,则是张浚刚刚亲自画的。
墙上挂满的画,也都是出自张子初之笔。张浚很是欣赏张子初的画艺,对方的每一幅佳作他都会极尽全力弄到手,然后裱挂在卧室之中,早晚赏析。
所以,张浚轻易能从左边这幅画里读出两个结论。
第一,这幅画故意隐藏了画中之人的样貌,作画之人似乎不想让朝廷找到这个人。
第二,这幅画绝不是出自张子初之手。
…………
“张子初啊张子初,没想到你我的命运竟会以这种方式重新交叠。”张浚秀美的面庞忽然拧出了一丝狰狞。他用指尖在桌面上敲击出一连串轻快的节奏,跃跃欲试地凝视着墙上的画作。
忽然指尖一停,形如鬼魅的身影顷刻间跪在了他身前,一共有五个。
他们个个都是身负绝技的高手,善于隐在暗处侦查,必要时也会动手杀人。张浚从一大堆案牒里抽出了第三张画像,递给了他们。
那幅画里的是个身形健硕,深目高鼻的男人,标准的契丹族长相。画像上还特别标注了此人右肩有伤,极易辨认。
没有人知道,除了马素素和那个身份不明的茶博士,还有一人也不曾落网。张浚故意让人放出消息,说他们从汴河里捞出了最后一具辽人刺客的尸体。所有人都以为,五个入池刺圣的辽匪均已经伏诛了。
接下来的这一步,才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张浚重新看向了墙壁上的那些画,唇边勾起了一丝微笑。
☆、八百里分麾下炙
璧月小红楼,听得吹箫忆旧游。
凤遥瓦舍外,一队禁军列阵而立。将士们身如松柏,面似石俑,除了偶尔马打响鼻,竟是一丝声音也没有。
前方倚马勒缰的年轻将军静静地瞧着自己面前的一顶官轿,似是在等待里头的人撩开轿帘。可等了半响,却仍不见有动静,以至于座下的马儿都开始有些不耐烦地刨起了蹄子。
将军抚了抚马颈上的鬃毛,使得它重新安静了下来。站在轿旁的厮儿冒着冷汗偷眼打量着马上的人,只见对方瞧来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已是眉飞入鬓,面如刀削,此时虽只穿的一身箭袖劲服,未挂片甲,却依旧掩不住那一股久经沙场的冷冽之气。
一双枭目信然一瞥,顿时让那厮儿背上一凉。
“范司直,魏将军到了。”在对方的灼灼目光下,那厮儿擦了擦额间的冷汗,冲着肩舆里轻唤了一声。
“范司直?”
可里头依旧没有动静。
莫不是要跟眼前这位摆谱儿?
厮儿正犹疑着要不要将那轿帘掀开半分朝里瞧瞧,一双手欲伸不伸时,却见一个身影忽而自马上翻身而下,阔步走到了跟前。
厮儿浑身一颤,下意识让开了半分。随着小将军指尖一勾,终是瞧见了轿中的光景。
端端一个瘦弱的白面儿书生,正靠着轿壁睡得香甜,头上的长翅帽歪了半截儿,嘴巴半张着,连流涎都快滴到官服上了也浑然不知。
厮儿这一看差点没笑出声来,只道这位新上任的司直,可真是个奇人。听说这位范晏兮范郎君,只因在金明池一事中同张子初一道立下了奇功,才从刑部一小吏一跃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