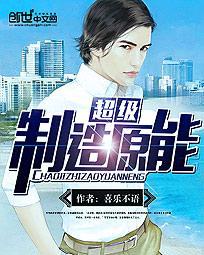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东京旧城 > 第92章(第1页)
第92章(第1页)
他两夜没合过眼,自己亦是如此,有什么可抱怨的?魏青疏这么想着,却没考虑到自己乃是铁打的英雄骨,对方却是纸糊的酸儒身,这一拽,倒把范晏兮整个人拽得往后一仰,如同一滩烂泥般软下了身形。
“范晏兮!我来看你来了!”冯友伦叫嚣着一进门,就瞧见范晏兮仰面倒在一男人怀中,双目紧闭,面色苍白。而那男人则双手紧搂着范晏兮,眼神凌厉之中又透出了几丝茫然。
“你们……在干嘛?”
魏青疏转头见到冯友伦正面色古怪地指着他们,脸色瞬间一青,一下子放开了怀中的范晏兮。只听见砰地一声,人摔在了地上,再无动静。
“范司直!?”魏青疏见他直直地躺着不动,又吓了一跳,赶紧蹲下身子去探对方的脉搏。
站在一旁冯友伦却是尤为淡定,只匆匆瞥了一眼,便笑着摆了摆手,安慰魏青疏道,“不打紧不打紧,只是睡着了。”
“睡着?”魏青疏不信,直到靠过去听清对方绵长的呼吸,又亲手切了脉搏,才将信将疑地站起身来。
“他这样也能睡着?”
“你还没见过更厉害的呢。”冯友伦冲他咧了咧嘴,二人合力将范晏兮抬到了后边儿临时休息的房间里,将人安置在榻上。
魏青疏看着榻上昏睡的人,见他眼下两块黑青都快挂到了脸颊上,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太过勉强他了。
“你先帮忙看着,他睡醒了再让他出来。”
“诶?你就这么走啦!”冯友伦还想着替好友讨一个说法呢,哪儿有这般逼人不眠不休上工的,何况这魏青疏也不是大理寺的官员。
他跟着魏青疏走了两步,二人还没走出房门,却听见咔嚓一声,头顶上传来了清脆的瓦裂。冯友伦一时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儿,正仰着脖子往上瞧,却见面前的魏青疏衣袍一振,踩着他的肩膀跃上了梁枋。
冯友伦被他踩得身子一萎,刚叫唤了一句,只见魏青疏抽出腰间的马鞭狠狠抽向了屋顶。哗啦啦,屋瓦瞬间被鞭出了一个大洞,上头一方黑影身形一闪,迅速往前奔去。
“屋顶有贼人!来人呐!屋顶有贼人!”冯友伦大喊了起来,一边去拖榻上的范晏兮。可任由他闹出多大的动静,榻上的人都如同睡死了一般毫无知觉,没办法,冯友伦只得一把背起了自家好友,半拖半扛将人弄出了屋。
出了屋一瞧,顶上已经乱了套。魏青疏正与一人打得火热,那人却似乎不恋战,拼命想摆脱魏青疏的纠缠。再往前看,还有两个黑影已经跃上了前边儿的围墙,一前一后逃了出去。
人群很快聚了过来,满院子的文吏指指点点仰头观望,候在院外的捧日军将士也迅速合围而上。
与魏青疏过招的是一个通体黑衣的高大男人。他此刻背部弓起,只御不进,却能在魏青疏如刃刺骨的鞭风里游刃有余。明眼人都看得出,魏青疏一人,怕是拿他不下。
这时候,魏青疏的几个亲信也先后跃上了屋顶。众人合围之下,那个闯入者明显开始捉襟见肘起来。一个将士举刀来砍,逼得那人侧身去躲,却不料被魏青疏看准了时机,啪嗒一下抽在他背上,差点将人从屋顶上抽下去。
身后又来两个将士,左右刀背一沉,便死死压住了那个男人。
“敢在捧日军的眼皮子下走梁,胆子倒是不小。”魏青疏冷哼一声,上前两步,刚要去揪那人,却是耳旁一阵风鼓,又从两旁瓦当下钻出了好几个黑衣人。
魏青疏眉头一紧,右手一抬,所有捧日军立刻严阵以待。冯友伦架着范晏兮浑身一抖,只闻几声叱咤,手执长矛的将士们便将他们以及架阁库的文吏通通围在了中央。
四周是密不透风的黑甲,严整的队形宛若一块铁盾,让他们心下稍安。
“将军且慢,吾等乃朝廷密探,奉命办事。”被按在屋顶上的那个人压低了声音,他的同伴随后曲膝而上,从怀中递出了一方令牌。
魏青疏接到手中一瞧,目光微闪,“清平司?你们是张浚的人?”
在魏青疏的示意下,将士们松开了地上的男人。那男人抬起头来,露出了一张有些沧桑的脸。
“是。”男人抱拳道。
“既然是张司丞的人,为何要潜入架阁库里。你刚刚说奉命办事,办的什么事?”
男人单膝跪地,久久不语。
“不说吗?那不如我来猜猜。你们既为密探,所做之事无非是跟踪,暗杀,寻人。那么你来告诉我,在这满是捧日军的架阁库里,你们跟的是谁?查的又是谁?”
魏青疏的语气开始变坏了。自从上头命令他和张浚协同查案以来,张浚连面都没露过一次,更别说与他商讨案情了。魏青疏本就对此人不爽,现在他竟然视自己如无物,堂而皇之地让他的探子进入捧日军所控之地。这个梁子,二人算是结定了。
男人知道魏青疏在气什么,可他偏偏解释不得。辽人还有落网之鱼一事是张浚吩咐不可外露的,如果此下让魏青疏知道张浚还对案情有所隐瞒,双方必将成水火之势。
“好,你不说也罢,等你们张司丞亲自来提人之时,我且直接问他。”魏青疏冷笑一声,让人将他们押了下去。
哗啦一声,警备的军甲在一瞬间退散开来。众人心中都松了一口气,而此刻,伏在冯友伦背上的范晏兮才悠悠转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