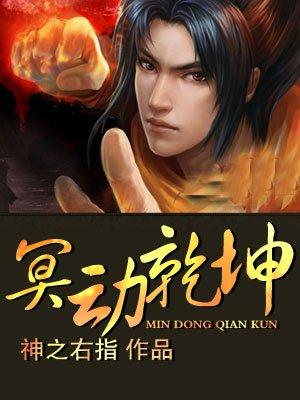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风起杨花儿 > 第3章(第2页)
第3章(第2页)
段成悦的眼神闪烁不定,过了半晌,道:&ldo;不必多礼。&rdo;
云姮站直身体,微笑道:&ldo;王爷,请进。&rdo;
她的种种仪态,乃至脸上神情微笑,都十分得体,段成悦看着她,顿了顿,往万锦阁内走去。云姮落后他半步,随之进入。
家宴却用的平静顺利,饭毕,撤下圆桌碟筷,另外换上檀木茶几,上好的清茶送上,原先王府内的侍妾、管家、丫鬟、下人,纷纷前来拜见女主,这番琐碎礼仪全部结束,已经快要到月上中天的时辰。
段成悦一直淡淡看着眼前一切,不动声色,到这时,缓缓道:&ldo;你们全都下去,我有话要跟王妃说。&rdo;
云姮眼中露出一丝诧异,向他看去。
众人立时便如潮水一般,静悄悄走了个干净,万锦阁内,顿时寂然。这种寂然对比着前一刻还在的无尽热闹,显得极是古怪,好像一场大梦,梦醒繁华尽。然而偏偏又不是梦境,精致富贵的宫灯尚在阁内发着熠熠光辉。
&ldo;你嫁过来也有几个月了,有一句话‐‐&rdo;段成悦轻啜茶水,仿佛随意地道,&ldo;我一直想问你。&rdo;
云姮微笑道:&ldo;王爷,您问便是。&rdo;
段成悦想了想,忽然也微微一笑,道:&ldo;你父亲是楚州首府,封疆大吏,你嫁给我的事,是你父亲做主,还是你自己情愿,抑或全然是陛下的意愿?&rdo;
云姮道:&ldo;自然是臣妾自己情愿。&rdo;
段成悦淡淡一哂,道:&ldo;事到如今,木已成舟,你是陛下钦定的定安王妃,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你只要说实话便成。&rdo;说着一顿,&ldo;我想听句实话。&rdo;
云姮略一迟疑,语气却仍旧很肯定,道:&ldo;臣妾确实情愿。&rdo;
段成悦看着她,忽地一笑,问道:&ldo;为什么?&rdo;
这句话本身就问的古怪,云姮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如何措辞,但是不能不答,一来为了恭敬,二来,倘若不答,就显得前面假心假意。她心中微微慌乱起来,正在想,段成悦又问道:&ldo;你想做王妃么?&rdo;
&ldo;这……&rdo;
一时之间,陷入僵局。云姮局促难安,终于道:&ldo;臣妾只有在心中敬慕王爷,能嫁王爷为妻,是云姮之幸。&rdo;
段成悦猛然站了起来,嘿嘿冷笑,道:&ldo;之幸?既然是幸,你就在心里好好考虑清楚,过得半载、一年,我死了以后,你剩下的四五十年时光,该怎么打发。&rdo;他快步走到门口,陡然又转头冷笑道,&ldo;你以为是你之幸?那不过是拿你来冲喜而已!&rdo;
话说完,伸手拨开珠帘,快步走了出去,哗啦啦一声,珠帘剧烈晃动,来回摇摆。
段成悦快步走到外面,深深吸了口凉凉的空气。那几句话发泄出来,登时舒畅了许多,心境渐渐稳定。
何藤升趋步迎上,小心问道:&ldo;王爷,今晚是回明净园,还是在哪位夫人那里?‐‐又或者,在王妃那里‐‐?&rdo;
重点自然在最后一句,段成悦打断了他,道:&ldo;回去罢。&rdo;
于是仍旧乘肩舆,回到日常休憩的明净园。丫鬟鬘姬迎接出来。此时已经到了万籁俱寂的时刻,一轮明月爬到中天,明净园里没有华灯灿灿,月光却也照得卧房内蒙蒙一片。鬘姬拢上菱花隔扇的窗户,服侍他更衣就寝。
不知道睡了几个时辰,段成悦在梦中倏然惊醒。睁开眼睛的一刹那,他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然醒来,只不过,渐渐地,感到心悸,汗水湿透了后背。梦中遇到什么,他已经忘记。实际上两年以来,不论前夜的睡眠多么香甜,到了后半夜,常常会满身大汗地突然惊醒,心脏在胸腔内狂跳,仿佛刚才梦中金戈铁马、命悬一线。
段成悦感到疲惫。湿漉漉的衣衫开始冰凉起来,他唤了一声:&ldo;鬟姬。&rdo;然而无人答应。段成悦叹了口气,他知道此时自己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他缓缓地从床榻上坐起,披衣起床,拉开了窗户。
这时窗外传进五鼓的更声。
段成悦在卧房内那张檀木大椅里沉沉地坐下,静待窗外夜色消散。
这是一天之中最难熬的一个时辰,因为他往往会在寂寞中想起很多。有时他会想起兄长睿帝;有时他会想起那杯&ldo;春寒&rdo;,直到两年以后的现在,他还经常会暗自诧异,怎么会如此无畏地接过&ldo;春寒&rdo;,将它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