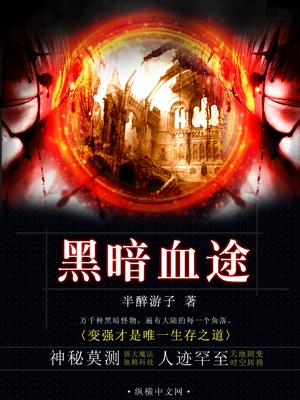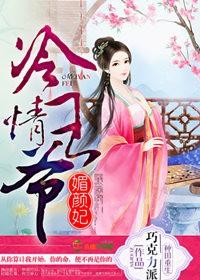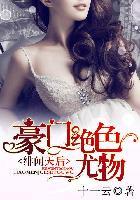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双钗缘第37章 > 第60页(第1页)
第60页(第1页)
有几片飘落在袁兆身上,划过他的肩头,落在骨节如玉的指间。他把玩着手中的树叶,细细摩挲着它的纹理。“树若倒了,依附于它的枝叶,焉能苟活?”他漫不经心道,“程奕再好,也撑不起程家这颗垂老的树,你有大好人生,何必执迷不悟?”“执迷不悟?”清懿兀自笑了一声,“好一句执迷不悟。”她的话意有所指,却教袁兆会错了意。他定定看了她一眼,忽然将手里那片叠成小果子的树叶递给她。清懿皱眉,不接。见她这副模样,袁兆轻笑出声,旋即便一撩袍角,随意往地上一坐。“你一个小姑娘,缘何总是这般老成?”他笑道,“倒是今日这番不听劝告,执迷不悟的作为,像个真正的年轻人。”清懿似笑非笑,看了袁兆一眼,“在您眼里,少年人的执迷不悟,想必是愚蠢至极。”“愚蠢?”袁兆像是思索片刻,又坦然笑道,“若说程奕,那确然有几分。”他又抬头看了看清懿,“你坐下罢,站了这么久,也该腿酸了。”清懿兀自站着,充耳不闻。袁兆也不再劝,反倒含着笑,淡淡道:“我既然出现在此处,周围便打点妥当,你不必担心清誉。”清懿一愣,她眉头微蹙,眼底难得有片刻怔松。没来由的,尘封的某段回忆好似被揭开一隅。袁兆此人,看似朗月清风,于细微处却有极敏锐的心肝。那时,距御宴初见过去不久,原以为人多口杂,总要传出一丝风声,说她刻意接近袁兆之类的话。后来才知,是袁兆打点好了一切,让人三缄其口。第二回见面,是在一个雅集上。也是如曲水流觞宴一般,男女宾客各一席,共同拟题作画。有好事者提议,不如以在座各位往日之作为题,再男女对调抓阄,抽中何人,便作何人的画。得了画主人的好评,便算作过关。清懿虽坐在不起眼的角落,可因着素日才名,人人都关注着她抓阄。展开手中的纸团,只见上面赫然写着──琼林夜宴图。短暂的寂静后,众人兴奋的眼风四下传递!这副画,有袁郎君珠玉在前,哪里能轻易超了去?况且袁兆恃才傲物的声名在外,想得他一句好,真比登天还难。公子们难得看一贯清冷如霜的大才女吃个闷亏,到底存着看戏的心思。贵女们却有些艳羡她的好运道,能抽中袁兆的画。各人轮着抽了遍,就剩袁兆和末席一位公子没抽。那公子起初推诿好几次,一直等旁人报了手中的签,这才断定剩下两个中必有清懿的。他瞅准了要拿某一个,却被一只手抢了先,他疑惑望去,只见袁兆似笑非笑瞥了他一眼。公子:“……”果然,那张纸条写着:《嗅青梅》。他二人竟成了场上唯一一对抽中彼此画作的。一时间,众人脸色都有些复杂。清懿有些意外,隔着重重人影,她微微抬头望向上首,却正正对上一双含笑的眼。山林间有花香顺着清风钻入鼻腔,有累垂于树木之上的层层花朵,落下漫天桃色。有一枚花瓣,落在清懿的裙摆上,飘落于小溪,顺着水波荡漾,晃晃悠悠,如同一只满载温柔的小舟,恰好驶向上首某位白衣郎君的身前。他恰好伸手捞起一捧溪水,那枚小小花瓣,就这样盛开在他的掌心。至晌午,已有数人画毕。众人纷纷找了对应之人品评。场中唯余清懿二人还未结束。在翘首以盼下,袁兆率先搁笔。有人伸长了脖子去看,只见他愣住片刻,惊疑道,“这……袁郎可是记错题了?”“嗅青梅是闺阁女儿画,怎么……袁郎画山画山画草原,就是没画青梅啊?”众人纷纷围观,七嘴八舌讨论。袁兆兀自坐在一旁喝茶,不发一语。唯余清懿闻得只言片语,如同感应到甚么似的,笔尖一顿。旋即,她看着笔下的《琼林夜宴图》,释然一笑道:“我画好了。”众人又凑过来瞧她的画,短暂的寂静后,有人憋着气道:“曲姑娘和袁公子,是不是故意耍我们啊?”他举起清懿的画,然后展开,只见上面画了一副北燕堪舆图。有人善解人意道:“想必他二人觉着彼此名作已然登峰造极,不好再擅自改创。”“啊,言之有理。”有不想得罪人的赶紧和稀泥,这事就翻篇了。宴席仍在继续,却有两个人在一片热闹里,寂然无声。原来也会有人以一叶的凋零而窥得秋日来临。御宴时,她说:“我想画内宅之外,京城之外,武朝之外。”于是,他的嗅青梅,是大漠孤烟直,是洞庭山水色,是一个小女子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野心。同样,清懿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何在画琼林夜宴时,脑子回想的不是那副描摹千百遍的恢弘殿宇。而是那晚寂寥月色下,他眼中辽阔的疆域。她的琼林夜宴,没有歌舞升平,唯有悬于他心上的烽火狼烟,百姓困苦。一场宴会从开始到结束,在旁人眼里,他二人不曾说过一句话。唯有那片落花知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短暂的自由只能维持片刻,回到家中,她又是困顿于四方天空的断翅之鸟。可这回却不同。或是隔日,或是天,院外不时有小玩意儿送进来,搁在她的窗外。末尾署名曲思行。今日是上好的颜大师字帖,明儿是一方好墨。都是贵重却不显眼,又能与她聊作慰藉的东西。她心下狐疑,深知大哥是个直肠子,绝对没有这般好品味,于是忍不住探查起来。终于有一日,被她逮着送东西的人,原来是她院里新买来的丫鬟。那丫鬟在逼问下,仍吞吞吐吐,最后涨红着脸说,“公子嘱咐我,不能随意告诉旁人。因为姑娘的清誉贵如珍宝,他想让你在内宅能舒坦一些,却又不能让你为难,所以才假借少爷之名。这样一来,既不会有旁人为难你,你自个儿也不必日日将这点好处悬于心上。”“他想你好,是想你真的好,并不是要你记他的好。”小丫头磕磕绊绊表达着,词不达意。可清懿何等玲珑,早便猜到是谁。她心中忽喜忽悲,默了良久才道:“我明白。他待我好,却不愿教我知道。怕也觉得,若得了我的欢喜,也是一种负担。”她这话没有自怨自艾的情绪,正如看透了事物本质的人,对于表层的情感,也就没甚么好留恋的。于是,她让小丫鬟把东西退了回去,又道:“多谢袁公子的赏识,我知他惜才之心。可惜……”她顿了顿,深吸一口气,再抬眸,露出一个坦荡的笑,“可惜,我对他的心,并不清白。故而,我不能同他做知交好友,请你将话转告给他。能得知世上有一人,懂我的志向,怜我的遭遇,已是平生之幸。如此,便已足够了。”小丫头犹豫着,到底还是捧着东西传话去了。自那之后许久,都不曾再有东西送来。看着窗前梨花满树,清懿想,这样结束也很好,斩断那一缕不可能的妄想,也是好的。直到有一回,她去亭离寺为娘亲祈福。幕天席地间,她放飞那盏孔明灯,忽然就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俗话,此刻若诚心许愿,或许能愿望成真。闭上眼的那一刻,其实她还没有想好愿望是甚么,脑子乱糟糟的,于是随意默念:想看到一轮最皎洁的月亮。再睁眼,往空中一瞧,结果乌云蔽月,灰蒙蒙一片。清懿难得有几分孩子气,嘟囔道:“果然是骗人的,哪有甚么皎洁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