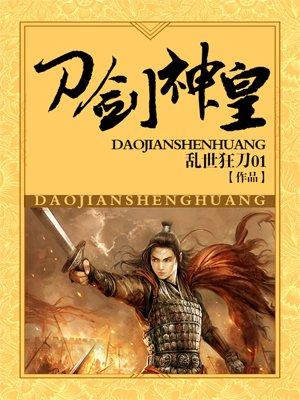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荷兰暴力事件 > 第10章(第1页)
第10章(第1页)
这个场面并不戏剧化,然而是梅格雷经历过的最奇怪的时刻之一。巴斯的眼光在他的脸上逗留了一会儿,他显然在踌躇。
那是毫无疑问的。他想要请探长同他一起到他的船上去。
船上有一个嵌着橡木护壁板的小舱,舱里装着罗盘和罗盘灯。
人人都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等候。最后,奥期廷张开嘴了。接着他突然耸耸肩膀,好像是在说:&ldo;真是荒唐的想法。&rdo;不过,他没有说这话。他用喉咙深处发出来的沙哑的声音说:&ldo;不懂……荷兰语……英语。&rdo;
仍然可以看到披着服丧的面纱的阿内伊的侧影,她在穿过运河桥,顺着阿姆斯特迪普运河拐过去。
巴斯发觉梅格雷在看那顶新帽子,可是看来他好像一点都不在乎。他的嘴唇上隐隐约约闪过一丝微笑。
梅格雷只要能用他自己的语言同这个人交谈,不惜倾家荡产,哪怕只谈五分钟也行。他在绝望中不顾一切,脱口而出说了几个英语音节,可是法语口音那么重,没有人听得懂一个字。
&ldo;不懂……没人懂……&rdo;那个刚才插过嘴的、形容憔悴的水手说。
梅格雷闷闷不乐地走开去,感觉到他已经接近谜团的核心,可是完全白费心思,这当儿码头耗子俱乐部的成员们渐渐地恢复交谈了。
几分钟以后,他回头去看那伙人,他们仍然在落日最后的余晖中闲聊,奥斯廷的脸给残照染得越发红得像火了。
到眼下为止,梅格雷一直处在‐‐可以这么说‐‐这个案件的外围地带,推迟着那次‐‐不可避免是痛苦的‐‐对一个丧事人家的访问。
他按门铃。六点多一点儿。他不知道那是荷兰人吃晚饭的时间,直到他在一个来开门的小佣人的肩膀上面看到两个女人坐在餐室的桌子旁才发觉。
她们两人息忙站起身来,马上但是相当生硬地表示有礼貌的态度。那种礼貌做姑娘的可以从家政学校里学到。
她们两人从头到脚穿着一身黑的。桌子上摆着茶具、几片薄薄的面包和冷肉。尽管光线暗淡,却没有开灯,只有煤气取暖器放射出来的光亮在同越来越浓的暮色较量。※棒槌学堂の精校e书※
是阿内伊想到开亮电灯,还通知那个佣人拉上窗帘。
&ldo;我真抱歉来打搅你们,&rdo;梅格雷说,&lso;尤其是在就餐时间。我不知道……,
波平加太太笨拙地把手向一张扶手椅一挥,困窘地望着周围,她的妹妹悄悄地走到房间最远的角落里。
这个房间很像他在畜牧场待过的那一个。新式家具,不过是一种不带夸张形式的现代风格:柔和的中性颜色,素净和雅致相结合。
&ldo;你已经来了……?&rdo;
波平加太太的下嘴唇在哆嗦,她不得不把手绢按在她的嘴上,捂住一阵突然的哽咽。阿内伊没有挪动身子。
&ldo;我现在不打搅你了,&rdo;梅格雷说,&ldo;我待会儿再来……&rdo;
她叹了口气,坚持留他待着。她花了很大劲儿,勇敢地恢复平静的神态。她一定比她妹妹要大几岁;她长得挺高,而且总的说来,更加女性化。
她的相貌是端正的,不过脸颊过分红了一点儿。她的头发有多处在开始灰白了。她的一举一动流露出受过良好教养的谦让的态度。梅格雷记得她是校长的女儿,而且她以非常有文化修养和能讲几国语言著称。可是这一切不足以使她成为一个老于世故的女人!恰恰相反,她的腼腆的尴尬相完全显示出她是小城市里的居民;明摆着她是那种对一丁点儿事情都会感到震惊的人。
他还记得她属于最严格的新教徒教派,,她通常担任德尔夫齐尔任何慈善组织的主席,还被认为是知识界的领袖。
她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不过,她用恳求的眼光望着她妹妹,好像求她来搭救似的。
&ldo;务必请你原谅,探长……真叫人难以相信,对不对……偏偏是孔拉德……一个受到人人喜爱的人……&rdo;
她的眼光落到房间角落里收音机的扬声器上;一看到扬声器,她差一点没哭出声来。
&ldo;这是他的主要娱乐,&rdo;她结结巴巴地说,&ldo;这和他的船,他夏天在阿姆斯特迪普运河上划船消磨黄昏。他工作得很勤奋……谁居然干出这样的事来?&rdo;
梅格雷什么话也不说;她继续说下去,脸稍微有点儿红,说话的声调可能是她受到责备后所使用的那种声调。
&ldo;我并不控告任何人……我不知道……那就是说,我不愿想……只是警察局认为是杜克洛教授,因为他拿着那把左轮手枪……我真的没有想法……这太可怕了。可是情况就是这样‐‐有人杀了孔拉德……为什么?为什么是他?甚至不是为了抢劫……那么,可能是为了什么呢?&rdo;
&ldo;你跟警察局说你从你的窗口看到……&rdo;
她的脸更红了。她站着,一只手撑在茶桌上。
&ldo;我当时不知道我该不该讲。我从来没有认为贝彻跟这件事情有什么相干……只是我当时恰巧向窗外看,我看到……我听说最不重要的细节对警察局也可能有帮助……我去问牧师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他说我应该说……贝彻是个好姑娘……说真的,我没法想像是谁……可是不管那是谁,那个人应该进疯人院。&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