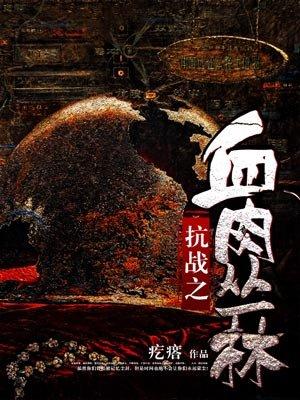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女主重生搞事业的 > 38 一波未平(第2页)
38 一波未平(第2页)
韩昭明白了,她提出让百姓直接参与考绩之事本来是为了保障百姓对朝中大事的知情权和对以自己赋税所养的官员考绩的参与权,却也忽略了重要的一点:舆论是一件利器,而官家也可以轻松地利用这一件利器,去劈开对自己不利的势力。
看来就算带着八年的记忆重活一世,她还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啊。
韩昭叹道:“如果可以的话,学生也想自揭身份,为燕王长史案平反,然后再把怀远的身份公诸天下,这样一了百了再无后患也好。
“可是,子曜一直并没有那么做,不是吗?”谢钧微微一笑:“因为直到你有足够的权力之前,直到民心的力量可以真正动摇皇位之前,做了这些事都只会是徒劳无功。”
所以,他们所有人都只能等。等待积聚足够实力,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如谢钧,如宋渝,也如她自己。
×××××
这时机,却是未免来得太快。
考绩的结果出来了,宋渝在集贤院修史可为不遗余力,判为上中等,赏赐九个月的俸禄,并跃为集贤院学士。谢遥为大理少卿期间公开审理扬州一案有功,深受扬州百姓爱戴,同样判为上中等,但他已官至四品,且年纪轻轻已是大理寺的副官,实在是挪不动了,所以只赏了俸禄,并无升迁。韩昭同样得益于南巡扬州的事迹,可是朝中对她这个胆大妄为的毛头小子的评价一向毁誉参半,便只评为了中上等,这四品官位本也是挪不动的了,不过也有三个月的俸银奖励。
俸禄赏银由太府寺安排各级京官和每年回京述职的地方官员陆续去领,不过由于考绩完结时已是十二月中旬,年关将近,这赏银便延后到年假之后才发放。
只是,谢遥连他的俸禄赏银也来不及领,便已经要匆匆离京。
只因,一直昏迷不醒的太傅夫人、怀远公子亲母,在十二月下旬终于撒手人寰。
本来对于皇帝的怀疑和他在豫州刺史身上做的手脚,谢氏父子相对上是处于被动,也没有什么相应的计划,只能静观其变。也幸好他们没有什么计划,因为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
谢府里本来为了新年而挂的大红灯笼被匆匆撤掉,换成了丧礼所用的白灯笼。由于红事白事不能相冲,谢府这一年是不会过年的了,也不会在年关之际大办丧葬之礼,便只在谢府正堂设了简单的灵堂给谢家父子的同侪亲友吊唁,然后谢遥便要赶在年关之前扶棺返乡。
这也代表着,谢遥在年假过后,便要开始为期三年的丁忧之期,必须立即解服辞官,回乡服丧三年。
韩昭在黄昏时分来到谢府,谢家父子其余的亲友同僚都已吊唁完毕回家去了,空荡荡的灵堂里只有跪在棺旁守夜的谢遥一人。
她静静地对着棺木作三拜之礼,谢遥也默默回礼。
韩昭把他拉起身来来:“人都走了,坐下说一会儿话吧。”
谢遥点了点头,许是跪得久了,双腿有些发软,身子便自然不过的挨在了韩昭身上。
韩昭恍若未觉,默默扶着他到一旁坐下。
她还未想到怎样开口,反而是谢遥先说话了:“母亲的身体早已油尽灯枯,只是没想到这日竟是在这当口到来。”
韩昭叹了一口气,神色凝重道:“宫中那位已经在怀疑你的身世,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