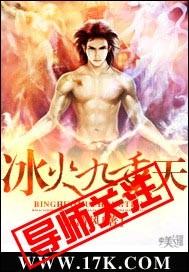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有双下巴的人有福气吗 > 第129章(第2页)
第129章(第2页)
陈医生靠向椅背,双手交叉在胸前:“可他是余行啊。”
第二人格表现得再怎么是余让,他也不会是余让。
“余行的内心很封闭,”陈医生接着说,“包括后面我再问询他有关他父亲跟余让死的那天的事情,他都说的很语无伦次,甚至前言不搭后语,他本能地想要忘掉,我怕更加刺激他,就没再追问。”
所以余让成了他思想的出口。
“那余让呢?”盛燃问得很艰难,“他对于……对于余让之死的态度呢?”
好荒谬的问题,陈医生捋了一把乌黑的长发,摇摇头:“作为这段惨剧里的死者,他的记忆是空白的。”
谁会愿意去面对自己的死亡,余让只有忘记自己死了的事实,才能作为独立的人格存活下去。
又有病人敲门进来,他们的对话终止,盛燃以为今天来这一趟能得到些许安慰,并进一步笃信自己把余让送进这里没有做错,可目前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他努力平复下焦躁混乱的心绪,精神类疾病的治疗原本就是一个漫长无涯的过程,如果他连开始都无法忍耐,以后的日子又该如何度过。
两天后他接到祁年的电话,不过电话那头是他弟弟。
“两个选择,”盛之乐连声哥都没叫,开门见山地威胁人,“要么明天回家吃个饭,要么祁年推着轮椅带我去找你。”
这声音中气十足,显然吃饱了。
盛燃焦头烂额得要命,但因为是盛之乐,还是控制住了挂电话的冲动。
“哥,”盛之乐嚣张完服软,“爸爸很想你,我也很想你,我们很久很久很久没有一起吃过饭了。”
盛燃并不怀疑他的执行力,毕竟当年身无分文就敢跑到小镇来找他。
“我选a,”盛燃叹了口气,“把电话给祁年。”
盛之乐哼哼唧唧不大乐意,还是乖乖照办,祁年接过手机走到后花园,问他余让情况怎么样。
“不太好,”盛燃没展开,问他,“我爸和乐乐知道我跟余让的事了吗?”
“你爸应该知道了,他没少叫人盯着你。”祁年出来没穿外套,这会儿冷得哆嗦,“明晚的饭局是你爸的意思,你应该能猜到他想跟你说什么。”
“非得让乐乐来开这个口吗?”盛燃觉得恶心,“他就不怕乐乐伤心?”
“乐乐他……他其实什么都知道,只是装作不懂。”祁年缩在墙角,“明天我去接你?”
“不用。”盛燃回绝,“乐乐这几天怎么样,听着心情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