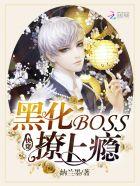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北荒山海卷攻略 > 第1页(第2页)
第1页(第2页)
旁边那人意识到不对劲,正想过去找黄毛,还没跨出步子便被陆荒一脚踢在肚子上,跌在一边。
黄毛咳嗽两声,撑着墙站起来,恶狠狠瞪着陆荒,“陆哥您这是干什么?我可不记得在哪得罪过你。”
陆荒走到他面前轻轻帮他把落在肩上的灰拍掉,“如果你现在滚,就是没得罪我,你要是不滚……”
“我滚,我滚就是了。”
黄毛给高个递了个眼色,两个人踉跄着跑了出去。
陆荒见他两跑得挺快也就没说什么,正想回去上课,却听见一直蹲在地上的那人在喊他。
“哥。”
他微微一颤,冰冷回答,“我不是你哥,再叫我一声哥,我就打死你。”
见身后那人不再说话,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到教室的时候谢顶严重的黄老头正在讲台上讲圆锥曲线,陆荒没打报道,从后门进去,径直走回自己的座位,然后趴在桌子上小眯了一阵。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讲台上的人已经换成了教英语的短发女老师,坐在他旁边一排的孙大头见他睡醒,从座位下面递给他两包小当家,他接过方便面,一股脑塞进课桌,又趴了下去。
老教室里既没有安空调,也没有装风扇,靠窗的位置热得像是烤炉。他睡不着了,就盯着窗外树上的麻雀发呆,脑子里乱糟糟的,不经意间又想起在厕所被打的那人。
其实他认识那人,那人叫莫北,是陆荒小姨陆雯的儿子,但他和陆荒没有哪怕一丁点的血缘关系,只是名义上的表兄弟。
陆雯幼年时父母因车祸离世,陆老不忍心见她四处流浪乞讨,将她带回家,一直养到十七岁她离开北川去沿海城市打工。
起初她还会给陆老寄东西和钱过来,后来就慢慢断了联系。陆老一生养育过两个孩子,一个是陆雯,一个是陆荒的妈妈陆玖,只可惜陆雯是个没良心的,陆玖找了个没良心的老公,两人都没能在陆老膝前尽孝,倒是陆荒这个孙子辈的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陆荒不喜欢那个自己从未见过的小姨,连带着也不喜欢莫北这个从大城市逃难过来的便宜弟弟。听到莫北管自己喊“哥”,他心里总觉得难受,像是有千万只蚂蚁在上面爬。
但不喜欢归不喜欢,他又不能真的把莫北赶走,看着这没用的小少爷饿死在街头。
想到这,陆荒忍不住皱起眉头,直到下午放学心里还憋着一股火,没等做值日大孙大头就一个人回了家。
他家住的房子比学校还要大上几十年,三间屋一个小院,院子门口用两块被虫啃得有点烂的厚木板当门,在木板上掏两个洞用来挂锁。
陆荒进了家门,先把院子里的鸡鸭狗喂了,然后准备生火开始做饭,土灶刚被点燃。
房门被人从外推开,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的莫北穿着又破又脏的短衬衣站在门口,朝着陆荒的方向很是可怜地喊了一声。
“哥。”
陆荒被这声“哥”叫得心烦,正想冲莫北发火,看到他身上的伤又下不去手,索性不搭理陆荒,起锅烧水蒸饭。
见陆荒不理自己,莫北一个人背着包进了里屋。等陆荒做好饭,端进去的时候,他正趴在屋子正中央那张吃饭用的桌子上写作业。
“吃饭。”
陆荒轻咳一声提醒他,把米饭和现炒的土豆丝摆上桌。
莫北闻言把书收起来,转身去厨房给自己盛饭。陆荒喜欢安静,一顿饭下来,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
大西北夏季的白天很长,吃过饭后已是晚上八点,但太阳依旧高高悬在空中,没有半点要落下去的意思。
陆荒叮嘱莫北把碗筷收拾干净,自己骑着家里唯一一辆老自行车去几公里开外的乡镇医院看望外公。
老人家上了岁数,身体一直不太好,半个多月前因为心梗晕倒在家里,差点没能醒过来,送到医院以后医生说了一大堆陆荒听不太懂的话,最后给出的结论是住院观察,最少也得住半个月。
因为链条生锈,这辆老旧自行车骑起来相当费劲,从走了十来米就开始咯吱作响,路过村口摆摊的商贩时,陆荒买了袋苹果,又在卤味店给老人家买了个鸡腿,匆忙把袋子挂上车把手后又吱呀吱呀地向着镇里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