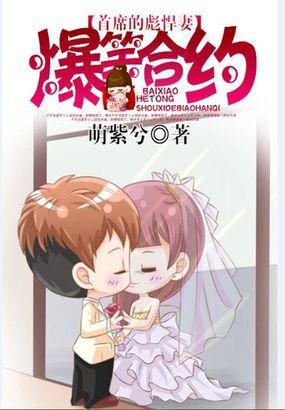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公公是傻子儿媳照顾 > 第1章(第2页)
第1章(第2页)
最主要是他打了她。
是以一回来,鹿白就怏怏不乐,见了谁都不说话。甄秋好心地凑了过去:“小白,谁欺负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骂他。”
鹿白瞥了他一眼,哭丧着脸不说话。放到别人那儿,多半就是“说出来主子给你撑腰”,在他们这儿,别说主子给你撑腰了,连主子都没人给撑腰。顶多就是说出来心里松快松快,再得别人两句安慰罢了。
“甄秋,”鹿白抿着嘴,像是要哭了,“我让人给打了。”
甄秋吓了一跳,仔细打量了一番:“谁啊,打哪儿了!”
他可从没见鹿白这么难过过,还以为是哪个太监宫女,见她长得傻气,又欺生,对她怎么样了。
鹿白的嘴角撇得更厉害了,说话都带了哭腔:“典刑司……”
甄秋不解了:“你犯什么事儿了?”
不管犯什么事儿,也该先找主子报备了再罚呀。何况小白怎么着也占了个六品女官的名头,再不济也不该沦落成这幅惨相吧?
鹿白姿势怪异地蹲在石阶上,随手揪了一片叶子在手里使劲揉碎,悲愤得不能自已:“我裤子还让人扒了,太不要脸了!”
前些日子整肃宫闱大行动,已经明令禁止了太监和宫女私相来往,更遑论肌肤接触了。今日竟然还发生这等宫女被当众扒裤子的行为,简直有违宫规,有失体统,有辱斯文!
“别说了!”甄秋一把捂住她的嘴,背上汗毛都竖起来了,随即立马意识到不对,忙甩开手,蹲在她半步远处,“怎么回事啊?”
鹿白扔了叶子,用脚尖点了两下,没精打采地开始复述方才极其屈辱的经历。
严格说来,扒裤子的小太监是无辜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叫窦贵生的恶鬼。
鹿白早就听说过窦贵生的名头。
进宫第一天她就知道了,这宫里除了主子们,不能惹的还有一位,就是司礼监秉笔、典刑司掌印,太监窦贵生。司礼监秉笔说来好听,是圣上面前的红人,实则跟他们底下人没什么干系,最多不过是感叹两句“啊圣上真宠窦公公”,然后巴结得更起劲了而已。且上头还有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压他一头,算来算去,他也最多称得上是个二把手。
但典刑司就不同了,宫中男女老少,凡是触犯了宫规的,都要被拎去典刑司处置。至于宫规谁来定呢,自然是窦公公;至于有没有触犯宫规谁来定呢,自然是窦公公;至于怎么罚谁来定呢,自然还是他老人家。
这可是性命攸关、杀头掉脑袋的大事,由不得大家不怵,也怨不得窦贵生能在宫里横着走。
譬如方才,单单因为看她不顺眼,就二话不说,直接把人临到典刑司打板子了。至今她都不知道自己是遭的哪门子殃。
甄秋的声音颤抖得像吃了弹簧:“谁?”
鹿白道:“就窦贵生啊,你不认识吗?”
空气霎时凝固了,半晌,对话才得以继续。
“你怎么招惹他了?”甄秋虽然胆战心惊,但仍不免好奇。
“我知道就好了!”
认真算起来,这还是她第一次仔细端详传闻中的恶鬼。他立在那儿,像一张空白的信笺,任人涂上几笔什么都可以。从他身上读不出任何情绪,一眼过去,转瞬间就能忘个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