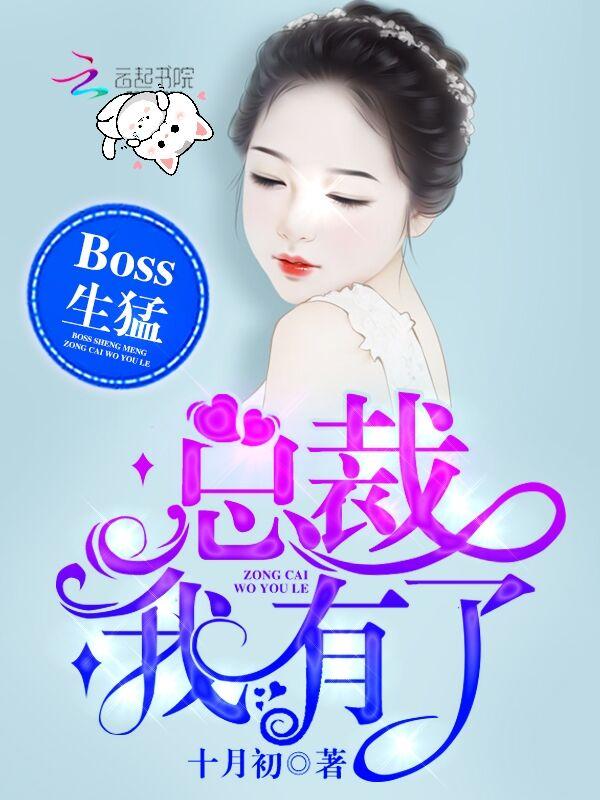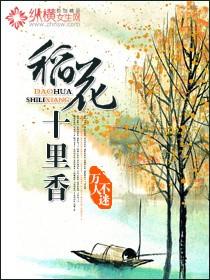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双钗缘全文免费 > 第110页(第1页)
第110页(第1页)
彩袖:“许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呢?”碧儿缓缓摇头:“要致人死地的阴毒法子,务必一击即中才好,怎会将机会系于姑娘的一念之间?若姑娘不动身,她筹谋的圈套岂不白费?”翠烟皱眉道:“此话虽有理,可反过来想,未必不是她事先筹谋好,正巧赶上了好时机。须知若不是姑娘福泽深厚,遇上袁小侯爷,可不就如她所愿了?”“再则,姑娘若出了事,以姑太太的手腕,十个咱们也不是对手,商道还不是她的囊中之物。”翠烟道,“你且看,她自知道姑娘出事,可有派人相助?四姐儿那样声势浩大地出学堂,她焉有不知之理?”一时间,众人出现了分歧,于是都安静了下来,等着上头的人说话。清懿仍然垂着眸,有一搭没一搭地拨弄着手炉,“翠烟,这两日守好院子,别叫人知道我回来了。再派人去盯着周边,甭管府里的,外头的,只要是有爱打听事儿的面孔,记得留个心眼。”翠烟领命去了。碧儿迟疑地问道:“姑娘可有疑心姑太太?”清懿的手指规律地敲击桌角,闭着眼睛淡声道:“不必理会,且等上两日,我就晓得她是不是。”昨儿回来时,清懿便避开了旁人,只有翠烟彩袖几个亲信知道。接下来的两日,整个院子守得铁桶一般,陈氏那头有几个婆子探头探脑,俱都只闻得流风院出事的消息,到底出甚么事却是不知。这天傍晚,翠烟的盯梢有了结果,正急匆匆地要禀报,外头却传来消息——国公府姑太太到了。众人闻言皆是一惊。虽不知曲雁华这个时候来作甚,清懿倒没有半分异样,随意道:“请进来罢。”半盏茶的功夫,盛装打扮的美貌妇人娉娉婷婷而来,假惺惺地寒暄一番做做样子。等门一关,彼此都懒得再装。清懿率先问道:“姑母贵脚踏贱地,所为何事?”曲雁华略抬手,扶了扶晃动的流苏步摇,不紧不慢道:“来自证清白啊。”“哦?”清懿用茶盖撇了撇茶沫子,细细品了一口,轻笑道,“姑母竟也知道自己的嫌疑颇重呢?”曲雁华挑了挑眉,一双含情美目此刻却满含兴味,她惋惜道:“倘若你真的出事,我便顶了这个黑锅也没甚么,高低有好处。可你现下好端端的,我要是平白被你疑心,引得你报复我,我倒亏狠了。”清懿哼笑一声,撩起眼皮看她,“没死成,不如您所愿呢。”曲雁华也抬头望向她,对视的一瞬间,彼此眼神中的锋芒悄然碰撞。良久,曲雁华缓缓收敛笑意,眼底一片冷静,像是摆出了真正的本色。“不是我,信不信由你。”她淡淡道,“我若想置人于死地,必不会给她留有生机,哪怕只有一丝一毫。”清懿低着头,闲适地窝在狐狸毛软垫里,沉吟不语。屋内,敬亭玉露的茶香四溢,曲雁华却无心品尝。没人说话的时候,耳边只剩下银骨炭燃烧发出的“哔剥”声。她端庄地坐着,背脊无意识地挺直,静静等候着上首那个小姑娘发话。仅她一句信或不信,就能决定堂堂国公府二奶奶今后的路好不好走。“姑母松泛些罢,凡事都憋着劲,累不累?”清懿往火盆里加了两块炭,一边理着火堆一边漫不经心道,“倘若我是你,心腹大患进入必死的圈套,何须再画蛇添足?有没有留下蛛丝马迹不打紧,横竖是死了。”“可现下的这个局却不是以结果为目的,它好像不满足于让我死,而是让我死的同时,盖棺定论为意外。”清懿缓缓道,“显然,我们即便察觉出了异样,可是到底没有根据,连我自个儿都忍不住想,是不是太倒霉了而已。可见幕后之人是决计不肯暴露身份,不是明面儿上的对家。”曲雁华在她开口的那一刻就悄悄松懈了防备,知道凝在自己身上的怀疑总算消失了。她端起半凉的茶,并不嫌弃,轻呷一口才道:“你还真信天底下有这样的巧合?我瞧你这样故弄玄虚,倒像是心里有了盘算。”“瞒不过姑母,我倒也有疑心的,只是还欠缺切实的证据。”清懿目光凝在银骨炭燃烧后的余烬上,手指轻轻敲击桌角,“我听椒椒说,项府二姑娘与我同时失踪。”曲雁华眸光一动,闻弦歌而知雅意,“你怀疑项家?”“虽然项家那个丫头与你们有龃龉,却也不至于下如此狠手,还谋划细致至此。”曲雁华沉思片刻道,“起先我也曾往这上头琢磨,细想却还是觉得牵强。”“你不必管她动机,我自有判断。”清懿垂眸,浅浅一笑,“哦对了,姑母既然来了,就顺带帮我做些事。以你的身份,想必在贵妇人圈子有几分人脉,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圣人突然出行的始末,只要事关项家女,一点儿细节也别漏。”曲雁华挑了挑眉,心中有几分狐疑,却到底没说什么,答应了下来。等她一走,偷听墙根许久的清殊溜了出来,往姐姐暖和的软榻上一钻,轻声问:“姐姐何需细查?项连伊有前世的记忆,她作恶的动机自是不必多说。”清懿塞了两个汤婆子到清殊的怀里,捏了捏她的脸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幕后之人是她无疑。只是……”她迟疑了一会儿才道:“我从前遭她暗害许多次,原先只道是她手段高明,就如这次一样,回回皆是巧合,叫人抓不住遗漏。”“如果说马儿发狂,山崩落石,丛林迷路都能归咎于意外,那么久病的圣人突然出行,好巧不巧还带走平日里并不受宠的父亲和兄长,就实在是突兀。”清懿缓缓道,“所以,我只想确认一件事,她是否真的有不寻常的手段,这种手段能运用到何种地步,咱们又要怎么克制。”清殊安静地听完,叹服于姐姐的未雨绸缪,走一步便想好后续的十步。她回想着见到项连伊的前后所有事情,反反复复琢磨,却偏偏抓不住一闪而过的头绪。越想越生气,清殊把头埋进靠枕里,闷闷不说话。清懿问:“怎么了?”“没怎么。”她瓮声瓮气道,“我只是一想到她前世那样对你,现在又这么阴毒,就气得发狠。平生第一次恨自己这样柔弱,不能成为一个会功夫的女屠夫,气不过的时候舍得一身剐,直接手刃了她去!”清殊突然想到那个有一面之缘的女子,英姿飒爽,一手长鞭甩得虎虎生风,要是她的亲人遭了这样的罪,想必早就打上门了。而自己还窝窝囊囊,手无缚鸡之力,什么也做不了。“世上女子千万种,有的是凌厉刀锋,有的是柔中带刚。有的是天上月,有的是林间松。你不必觉着偏要做哪一种才能痛快。你是个呛人的小辣椒,也顶顶厉害。”清懿摸了摸她的头,轻笑道,“安心罢,你不要小瞧了你姐姐。”“你也顶顶厉害。”清殊小声哼哼。她觉得,姐姐是温柔月,也是林间松,有时是包容一切的绵绵白雪,有时是杀伐决断的凌厉刀锋。—曲雁华的办事效率极快,几日后便打发人来递帖子,邀清懿过府一聚。席间,二人略略夹了几筷子菜,权当应了个赴宴的名头。闲话半盏茶后,曲雁华屏退了众人,眼底笑意尽收。“你所料不错,圣人此次出行颇有蹊跷。我昨儿赴了庆国公家的嫡长孙满月宴,他家袭爵的长子年前捐了个户部名下的郎中当着,席间吃醉了酒,说漏了两句嘴。传来传去,风就吹到了内院。话里话外不外乎是抱怨圣驾出行突然,顺手点了几个陪侍,都不是寻常的宠臣。”她转头道,“尤其埋怨你父亲和兄长。须知能陪圣人出行的,莫不是朝中重臣,他二人此番确然成了许多人的眼中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