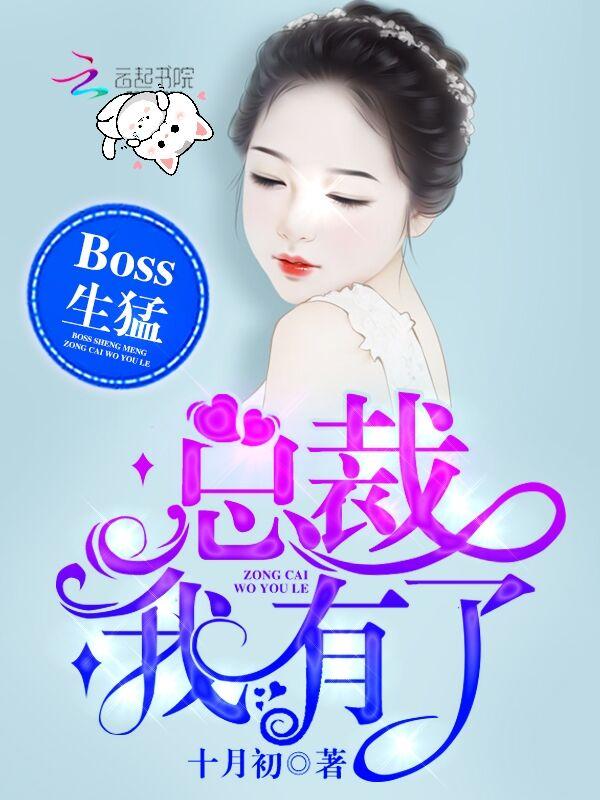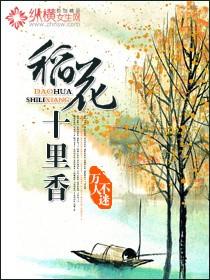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双钗缘全文免费 > 第118页(第1页)
第118页(第1页)
座中憋笑的不在少数,只有几个醉心诗文的人诚心拍手赞美。袁兆并没有笑,他垂着眸,耳边听着那人似哭似笑的嚎啕。“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他猛灌一口酒,摇摇摆摆环顾四周。他的声音渐渐低沉,又好像汹涌波涛藏匿其中——“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有一两个人没忍住,发出嘲弄的笑声。在这笑声里,他的语气越发急促。“醉折残梅一两枝,不妨桃李自逢时!向来冰雪凝严地……力斡春回竟是谁?!”满座的觥筹交错,富贵迷人眼。唯独他的眼神沉醉而清醒,他重复喃喃:“向来冰雪凝严地,力斡春回竟是谁……”待到最后一句收尾,他将酒瓶信手一扔,砸得粉碎,人也摇摇晃晃入了席。不知是有人捣鬼,还是自个儿没站稳,他“砰”的一声被拌倒,摔在花梨木几案上,鼻青脸肿。周围隐隐有哄笑声,这一刻,他像戏台上供人逗趣的丑角。袁兆下意识看向某个角落,少女的侧脸在明暗的光影里不甚清晰,只看得清她也没有笑,嘴角的弧度甚至是冷凝的。清懿摩挲着手炉,眼神落在诵诗人碎裂的酒瓶上,很快,有下人将碎片都打扫干净。因她坐在角落,能听到下人们的闲言碎语。“这是哪家公子?忒丢脸面。”“哪里是甚么公子,听说是哪家少爷带来的寒门子,姓裴。不过是借着雅集的风头哗众取宠的。”“我说呢,瞧他模样真是有怪病,自个儿都冻得发紫了,还抱着梅花不撒手,真不怕被刺扎啊。”“唉,别嚼蛆了,他是下人,咱们是下人的下人,来了这个场子的,都得叫咱们伺候。”说着,下人们便抬着他往外走,这人已经醉醺醺了,临到门口,不知怎的挣扎起来,抬手要找掉落的梅花。小厮不知其意,懒得理会,他挣扎得越发厉害,差点儿从抬人的架子上翻下来。众人不会注意丑角的离场,自然不会注意这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只纤细洁白的手,拾起那朵沾了酒气的花,轻轻递在他手里。那人浑浊的眼睛突然睁开,盯住眼前的人。清懿这才发现,这人凌乱头发下的脸,其实算得上清秀,只是酒意朦胧,多了几分狂态。“多……谢。”他含糊道。清懿垂着眸,微微颔首。“不必谢我。”她好像是不经意间开口,声音如霜似雪,“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陆游的诗,极好。”歧路(一更)◎姐姐交朋友啦◎宴至半途,盛瑾差人奉上以梅花点缀的各样小食酒水,供客人品尝。趁着这个空当,清懿唤来碧儿,“方才没顾上椒椒,想来仍是同盛二姑娘在一处,你去寻她来。这会子怕是要饿了。”碧儿领命去了。清懿虽记挂着妹妹肚子饿,自个儿却懒怠动筷子,略略尝了几口梅花蒸奶酥酪,便觉三分饱,不再饮食。耿三郎暗中注意着这头的情形,借着众人四散饮酒闲谈的契机,他状似不经意擦身而过,“呀,曲姑娘,饭食可是不合你胃口?一日三餐,午食最讲究饱肚,饿着可不行。倘若你吃不惯这里的,我家侍童倒还带了几样府上的点心,虽不是山珍,胜在有几分滋味,如何?”清懿垂头行了一礼,袖子下的手仍不紧不慢地摩挲着暖炉,“多谢耿郎君美意,小女心领。盛府的吃食别出心裁,不是它的缘故。我只因来时贪嘴,在家多用了几块糕,并不觉得饿。”耿三郎定定看着她说话时的神态,一时也没注意听她说了什么,只胡乱点点头,“唔”了一声,“啊,既然如此,倒也就罢了。”清懿察觉到他的眼神,眉头轻蹙,唇边笑意愈发敷衍。耿三郎还想说什么,却被突然赶到身后的老友猛地一拽袖子:“好啊耿兄,叫我好找,方兄他们都在等你呢,还不快去。”耿三郎还恋恋不舍,想要回头说些什么,却被连拖带拽地弄走了,那老友还顺口打趣了他两句,清懿隐约听到只言片语。“不过是个草包美人,你上回又不是没见识过……这回美之更甚,你就动心了不成?”离的近的几个姑娘听了这话,暗暗打量清懿的脸色,却只见她神情淡淡,理了理斗篷,往园外走去。有心肠软的看不下去,悄声抱怨道:“唉,我真真看不下去,上回这样,这回又这样。你们有所不知,曲家姑娘来京才半年功夫,前儿就因为不通才艺被挤兑了一番,闹得好生没脸。这会子,那几个才子佳人架势这样大,怕又要叫她难堪了。”有不知内情的打听了起来,这人就细细将前事告诉她,一时间,这一圈儿姑娘家心中都不是滋味儿。虽然,她们是大家闺秀,平日里也学得几样才艺傍身,可到底不是拿来吃饭的本事,技艺自然说不上精湛。时下攀比风气太盛,年轻学生又好风雅之事,每每集会,她们这些个平庸之辈,哪次不是沦为了陪衬鲜花的绿叶。而鲜花一角,总归是固定几个出风头的人轮流当,诸如项连伊、耿三郎等。因此,热衷于办雅集的也就是这帮“鲜花”,谁又能知道绿叶的不忿呢?她们一代入曲家姐妹的情境,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冷不丁的,与项连伊交好的一帮贵女走了过来,“没本事的不知勤学苦练,倒在背后挖苦讽刺本事大的人,这是甚么道理?脸面都是自个儿挣的。她没脸是她的事,你们可要替她出头?”领头的女子是督察院左副都御史家的嫡女,因她父亲在项丞手底下做事,她又与项连伊是同窗,所以算得上是头号马前卒。这女子穿着绛红色百蝶穿花袄裙,满头珠饰,傲慢的眼神扫过一圈年纪小的姑娘们,直把她们盯得缩头缩脑,才满意道:“你们年纪小,掌教娘子还没教你们识人的道理,别瞧见个弱柳扶风的就生出怜人的心。”坐在角落里的小姑娘,原就是家世并不如何贵重的,又因年纪矮一头,哪里还敢多言,都垂着脑袋大气不敢出。“好了,莫要吓到她们。”项连伊隐在后面,这时才出头,一副斯文柔弱的模样,“妹妹们别怕,我知道你们误会我,所以今日也想替自己辩上一辩。”她语气陡然低沉,眼眶微微湿润:“在旁人眼里,我爱慕虚名,事事要搏头筹。可我又岂是单单挣一个人的名声?“我虽虚长诸位几岁,却也算不得是聪慧。为了这些虚名,我在人后苦练技艺,下了不少功夫,为的只是不让男人将咱们女子看轻。”小姑娘们渐渐听进去,抬头看向她。“雅集自古有之,仰赖天家宽仁,特开女学,让咱们女子同男子一道谈诗论画,这是何等殊荣。既然有如此之幸,咱们自然要齐心合力,哪能为着一些小事生出嫌隙,叫人看笑话?”项连伊言辞恳切,目光所及之处,姑娘们脸上隐隐有愧色。“连伊姐姐,是我们不懂事了。”有人低声道。“对,是我们误会姐姐了。”道歉接二连三。项连伊仍然是那副温婉的神情:“无妨,你们年纪小,慢慢就懂这些道理了。”小姑娘们顿时佩服她的气度心胸,倒有几分真心实意爱戴她了。唯有最开头说话的圆脸女孩冷冷淡淡,不为所动,并不参与她们突然火热的畅聊。项连伊余光瞥见这一幕,冷了一瞬,复又笑容和煦,越发热络地同旁人说话。没一会儿功夫,角落里的氛围掉了个儿,其乐融融一片,笑声能穿过窗棂传出院门去,不远处,避着风雪的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