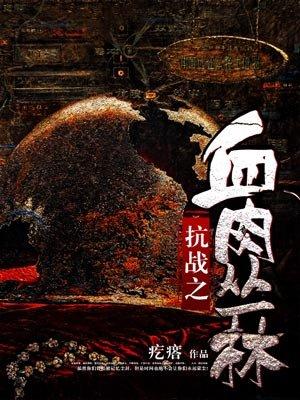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东京是什么? > 第17章(第1页)
第17章(第1页)
这会儿驴子停了,才发现驴上的竟是一古怪书生,更是摸不着头脑了。
马上的将军上下打量了一番面前的几人,眉峰一横,冲着骑驴的范晏兮沉声道,“何人胆敢冲撞禁军,不要命了?”
范晏兮见状,不急不慢地抖了抖袖子,悠悠翻身下驴,对着不远处的张子初信然一指,“此人有要事,需得拜见将军。”
张子初无奈地露出一丝苦笑,只见那将军虎眼一眯,手一抬,他身后的骑卫唰唰勒马而上,有条不紊地将他们几人围在了宝津楼前的空地上。打着圈儿的骑兵个个训练有素,里一层外一层,左右反向而行,渐渐收拢当中的围圈,只要当中的人稍有异动,便即刻会被踏成肉泥。
“将军息怒,在下确实有要事相求,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张子初一拱手,俯下身来朗声道。
那将军策马前行几步,在张子初身前停了下来。张子初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一道出,可对方的神情却丝毫没有变化,甚至连眉头也没皱过一下。
“有人被挟持,应是去落雁楼通报建安卫才是,你们如此乱来,可知该当何罪?”将军身旁的副将呵斥着。
“被绑的,可是李相千金!”冯友伦忍不住反驳。
那将军闻言,眉峰终是一挑,“你这消息从何而来?”
张子初看向一旁的范晏兮,只见他微微点了点头。
李相家的千金……怪不得范晏兮要如此胡来,将这些将士引至此处。看来,事态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冯友伦见张子初低头不语,似是在斟酌些什么,更加心急起来。
“子初兄,你再不把那东西拿出来,说不定咱们就小命不保了。”
张子初伸手去摸腰间的东西,微微捏紧了指尖。面前的这些骑兵,是殿前司禁军的捧日军,为上四军之首,属精锐中的精锐。而这将军,名为魏渊,乃捧日军右厢指挥使,更是常伴圣驾,恩泽浓重,若有他们相助,只要找到了那群贼匪,定能很快救出人来。
可捧日军从来只听皇命,只卫皇权,就算被绑的真是相门千金,他们也没有义务去插手。要想让面前的人出兵相助,就只剩下一个办法。
冯友伦和范晏兮都知道,这是张子初最不愿意用的办法。
但他们更知道,依照张子初的性格,别说人是在等他的时候被掳走的,就算不是,这事儿他也必定会管到底。
很快,果见张子初又深深叹了一口气,终是从腰间掏出了一枚银色的鱼袋来。
魏渊瞧见那鱼袋子,面色蓦地一变,终是从马上起下身来。朝中官员,但凡能授此鱼袋者,必是五品以上大员,可面前的书生年纪轻轻,面相甚生,不似是朝中之人。可就是这样,才更从这鱼袋子上看出了不同寻常的恩宠。
葛大头这头带人溜达了一圈,屁也没找着,正按着约好的时辰到了宝津楼前,就瞧见了这场面不小的一幕。
“草民张子初,刚刚多有得罪之处,还望魏将军海涵。”
“葛头儿,张子初是谁?这书生看上去来头不小啊。”葛大头身旁的厢军偷偷地问道。
“哼,何止是不小,没瞧见一向鼻孔朝天的魏大将军见了他都要下马。”葛大头摸了摸鼻子,对身后人一指,“咱们这回,可算遇上贵人了。”
“这小子究竟何方神圣?”
“蓬莱文章建安骨,诗画双绝张子初,东京城里三岁孩童都知道他,你小子平日里除了赌钱还他娘的在干些什么。”
“原来是张大才子,幸会。”魏渊听到张子初这三个字,终是明白了过来。
东京城中,若论起翩翩儿郎,谦谦君子,人人第一个提起的便是张子初的名字。因其才华横溢,更是被蔡相所重,几次欲征辟入翰林画苑,可他却屡屡推脱,不肯入仕。世人多传其人淡泊明志,行隐士之风,一时名声更是大躁。
圣上甚至钦赐了他银鱼袋子,说是等哪一日想通了,便可携袋前来。
无官职者身挂鱼袋,这还是古今而来的第一人。
“将军过誉了,若不是张某一介书生,百无一用,也不敢劳烦将军。可此下救人如救火,怕是片刻也等不得了。”
“自然。”魏渊点了点头,随即又道,“张公子可能确定,被挟持的就是李相千金?”
张子初闻言又瞥了眼一旁的范晏兮,只见他依旧是一副浑浑噩噩的样子,一把扯过人来,微微笑了笑,“这位是刑部检校从事郎范晏兮,他说是李相千金,就一定是李相千金。”
范晏兮缓缓转过头来,见他笑容尔雅,无所谓地点了点头。他左右不过只是个刑部小吏,到头担起罪责来怎么也轮不到他头上。
“既然这样,那魏某这就派人去寻,不知这些歹人可有什么特征?”
张子初想了想,缓缓道出了一句在心尖儿上盘算了很久的话。
“那些贼匪……似是辽人。”
张子初轻飘飘的几个字,让魏渊面色剧变,“你说什么?!”
“那几人深目高鼻,长面窄额,汉语虽练的流利,可手上虎口间却多有裂伤厚茧,应是长期执缰勒弓所致。”
“……你可看的清楚?”魏渊下意识地握住了身侧的佩剑问。
“将军稍等片刻。”张子初说着掏出随身的画具,寥寥几笔,便勾勒出四五人来,其貌状鲜明,若人立于前,同张子初描述的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