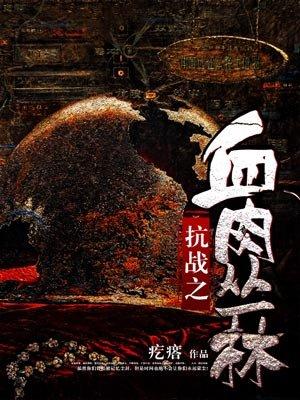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春寒青山遮不住评论 > 第47页(第1页)
第47页(第1页)
这几年的相处,甚感激你的细致孝顺,上天赐我缘分与你结为父子,定会再助我长寿,活到与儿重逢的将来。保重!父胡孝存字&rdo;世间事,仰恩最恨别离,偏偏你越恨越怕,它越是要跟要随。乱世漂浮,中国又如此之大,一别之后,要多少年才能再走回从前?父母,尚文,四爷,玉书……谁又能说清楚,哪一次匆忙分手就无意成了永别?只是匆匆地说了再见,便永生再不能相见,这人世之间,我们能把握的究竟有多少?船舱的门,被有规则地敲了几下,凯特确实跟他说过敲门的暗号,可当时因为心惶,却没怎么记住,仰恩被那细小的敲门声惊得全身紧绷,急忙掏出了怀里的枪,因为上满膛的子弹,有些重,又一次向他受伤的肩膀提出挑战,只是紧张时刻,已经想不了那么多,手臂是颤动不止,枪也抖个不停,连呼吸也全然忘记,门外的人却没了动静,片刻之后,门才被慢慢地拉开了。光线象是泄洪闸的水一样涌了进来,原来不知不觉,外面亮了天他也不知,那人高大的身躯堵在门口,镶嵌在一片金色的阳光之中,象个巨大的发光体,让人难以直视,仰恩不禁侧脸避开强烈的光线,手上的枪却不敢放松。直到他听到一声低沉却无比熟悉的亲切呼唤:&ldo;仰恩!&rdo;一别三年,之前构思的种种重逢,都与今时今刻这般不同,这种难以预料的差异,让两人一度无法确定,面前的人是不是真的站在自己眼前,而不是多次梦里水一样缥缈的相逢,梦醒时,雾般消退得无影无踪。崇学贪婪注视着仰恩的精疲力竭模样,心里又觉温馨,体力已经透支到如此地步,听到自己从赶过来并未通知上级的时候,还不免似批评一般地说了一句:&ldo;你可是疯了?&rdo;&ldo;一见面就给你用枪指着,现在又说我疯,我看你不是真心想见我吧?&rdo;&ldo;哪有想见就能见那么简单的事?说老实话吧,你是不是给人撤了?&rdo;&ldo;三年不见,倒变得多疑,不是跟你解释原来战区的防务转交他人,重庆调我去新开辟的战区,这次是去香港接待一个国际代表团,他们要两个礼拜后到香港,我呆不住,就顺便来接你。&rdo;仰恩的责怪完全是出于对崇学的安全着想,只琢磨着他确不是莽撞之人,似乎一直也没离开这船,大抵也是躲在哪个秘密船舱里,等着自己。再想这船上的部署,必定是安插了不少保安的人手,既然连关系密切的凯特小姐也不知道他到上海的消息,恐怕也是极端保密,就算四爷也未必知情,如此看来,确实没有外人能得知,自不会有太大危险了。这颗心百转千回,才慢慢放下来。虽然巴不得时时刻刻这么盯着爱人,无奈这一夜的折腾却累得他睁不开眼,崇学明显也不想打扰他,只沉默看他闭目养神,长久的分离,那本来以为积攒了满腔满腹的话语,此刻竟不急于表达,只要安静地坐在一处,只要手与手相连,只要呼吸在一起,心跳在一起,只要我们都还为了彼此,勇敢地活着……仰恩觉得自己似乎睡了一会儿,又似乎很清醒,不知道是梦境还是现实,崇学的味道春暖花开一般包围着自己。他的手摸索了一阵,抓住那人略嫌粗糙的掌,此时,外面传来一声悠长的鸣笛,船开了。&ldo;我想你,丁崇学,&rdo;迷迷糊糊地,仰恩说着,&ldo;想了你三年了。&rdo;崇学嘴上没回应,只伸手抱住了他,又碍于他的伤,没敢抱得太紧,轻轻把他的头按在胸口,任他听自己沉重连贯的心跳,每一下,都呼唤着他的名字。不久有人规则敲门,崇学没立刻开门,等了一会儿,才拉开道缝儿,门口隐蔽处放着两份午饭。仰恩那会儿的体温已经升上来,没什么胃口,却依旧在崇学的帮助下稍微喝了点汤水。由于双手完全不能用,这般就着崇学的手吃东西又觉得尴尬,只好说:&ldo;你放在一边,我手松快松快就自己吃。&rdo;怎料那人全不理会他合理的要求,一勺汤水又送到嘴边:&ldo;也不看看你那两只手肿得跟猪蹄差不多,等它们能用了,估计你也饿死了。快吃!&rdo;仰恩皱眉怒视着,还是乖乖地张了嘴,喝得有些堵气。稍微吃过之后,精神不济,他先是小睡了一会儿,渐渐觉得格外不舒服,咬牙忍了阵,只感到身上没一处不难受,想翻身又没气力,喘气都费劲,冷汗如雨,慢慢湿透了衣衫。一直观察着他的崇学很快发现他的异样,在耳边小声地询问:&ldo;挺得住么?&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