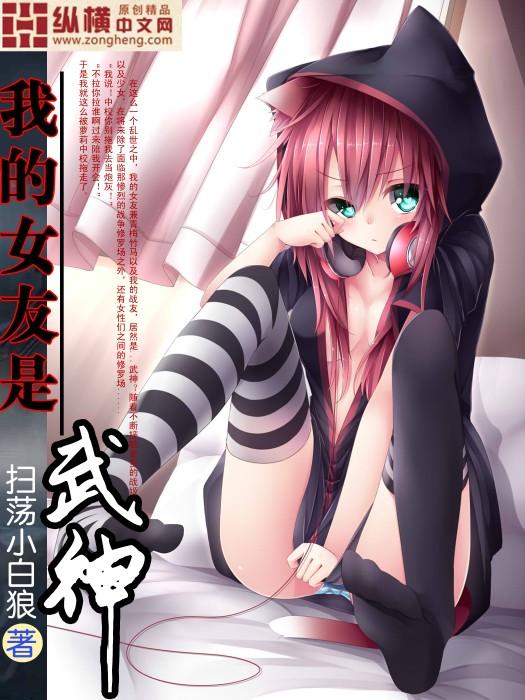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嫁到漠北以后类似 > 第83章 番外六(第2页)
第83章 番外六(第2页)
新婚当夜,新娘失踪不见,若传到外面,只会对女子名声无益。
“不能报官,我们怎么查?绾绾现在生死不明,你叫我怎么安心!”王氏担忧女儿,早已哭了一场,此时眼眶通红,帕子湿了透。
行严沉吟半晌,站起身,“岳父岳母,此事危急,现在还没查到小酒儿行踪,我是担心小酒儿叫歹人掳了去。上京贵女不少,贼人既然挑中了小酒儿,此时又没信传来,我怀疑不是为财。”
“不是为财又是为了什么?我的绾绾,哪个恶人把她掳了去!”王氏含泪道。
厅内一时沉默,沈岁寒长叹息一声,一瞬像是年老十岁。
“大人,来信了。”
厅外仆从来报,手中奉上一张信纸,“大人,方才有一群乞儿忽然要闯府门,仓皇间就将这封信丢下了。”
众人目光都落到信上。
沈岁寒眼一低,接过信笺,抬手让仆从出去。
纸上寥寥字迹,看完,行止先问道:“岳父,这信可是那贼人送的?”
沈岁寒点头,若有所思道:“信中说他们要借用行乙医术,一月后就会把人安全送回。”
…
几近入夜,马车停靠在驿站前。
沈瑜卿中途疼得没了知觉,再睁眼时是在一间燃烛的屋内。断掉的手臂重新接了回去,只不过她身上的衣服换了,防身的药全被搜刮了去。
服侍她的是不会说话的哑女,正揉她的小臂,手心抹了一层软膏。
沈瑜卿腹诽了两句,心想等她回上京必不让那个王八蛋有好果子吃。
“是他们让你来服侍我的?”沈瑜卿抬眼问出声。
哑女专注地给她上药,对她的话充耳不闻。沈瑜卿这才注意她原来也听不到。让这样一个人服侍,她想问也问不出什么。
一夜过去,日头高升。
哑女端饭食进屋置到案上,眼看向沈瑜卿,用手指了指她,又指了指热腾腾的粥。
沈瑜卿扫了眼,唇抿住,骤然间抬手拂袖,直将案上的汤水挥到地上,乒乓声响,哑女吓得心口跳了跳,喉中呀呀地说不出话。
地上的白粥冒着热气,沈瑜卿拍拍手,“让他过来,否则就算饿死我,我也不会吃。”
哑女不知她在说什么,手忙脚乱地收拾好地上狼藉,慌忙跑出去了。
好一会儿,一阵沉稳的脚步声传近,不是上京宦官世家的锦靴,反而比靴履的声音更加有力,掷地有声。
沈瑜卿侧坐在案后,支颐托腮,垂眸不知在想些什么。
很快,门从外打开,眼下是笔直结实的双腿,粗布的胡裤束缚,脚下如她所想,是漠北人才会穿的马靴。靴面沾染尘土,应是彻夜赶路所致。
“怎么,有饭不吃等着饿死?”男人声音低沉,有独属于他的粗。硬沙哑。
沈瑜卿稍稍抬眼,眸色浅淡,疏离嫌恶,“你倒底想让我做什么。”
“救一个人。”魏砚点了点刀鞘,“救完人,就送你回上京。”
“我要是不救呢?”沈瑜卿脸色不好,眼里隐有火光冒出。
魏砚从腰间随意摸出一块牌子扔到案上,咧了下嘴角,“不救,你的双亲,你新婚的夫婿,一个也逃不掉。”
沈瑜卿看他一眼,拿过金制的牌子放到手里,来来回回看好几遍,牌子上刻淮安王三字。
谁人会知年少离京,镇守漠北的淮安王,竟会做出这等虏人的勾当。
“就凭你是王爷又如何,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你先劫持我,就算告到皇上那也该问责。”沈瑜卿掀起眼,手中握紧那块令牌,眸色清冷。
魏砚抛下手中的长刀搁置到案上,屈腿面对她坐着,黑眸幽幽盯她,眼里有笑,“倒是个胆大的女人。”
“与我做个交易如何?”他问。
沈瑜卿白他一眼,“什么交易。”
“你想要什么?”他问。
“回京。”她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