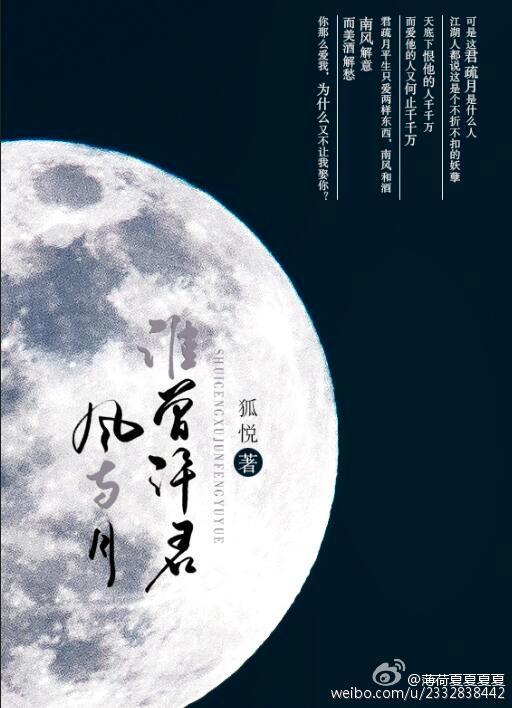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孔雀鱼多久成年 > 第2页(第1页)
第2页(第1页)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卢心尧是过了很久才听到卢承信的声音,他的声音听上去好远,那些水挤压了他的听觉,他像是被关在了一间狭小的黑屋子里,“在你很小的时候,卢从景很想杀了你……”卢心尧听得断断续续,他在心里摇摇头,小叔叔待他那样好,怎么会想要杀他,骗人也应该找个高明的理由。胸口扩散性地疼痛逐渐蔓延开来,他喘得更急了。再一次浸入水中,他已经听不到卢承信还在一张一合的嘴说了什么,只能听到自己雷鸣般的心跳声,心跳是那样掷地有声,带动指节的震颤。“……就是因为你出生了,所以卢从景要分一半家产给你,”卢承信继续说道,“像他那种人,怎么会允许有人夺取他的家产呢?”说的内容卢心尧已经完全听不清了,反复呛水让他失去了浑身的力气,好几秒都是完全无意识的。肉体的痛苦出于自我保护机制与大脑断连,仿佛只剩了一个苍白的躯壳还在那里挣扎,他以为他已经溺死在上一秒了。“信爷,不能再搞了,”手下为难道,“我怕再弄就不行了。”卢心尧养得金贵是众所周知的,现在看上去有点吓人,哪怕再次被压在水里也不怎么挣扎,体温降得比他们预计的快很多,摸上去已经没什么温度了,间隔极久才能再听到一次微弱的心跳。卢承信气得牙痒痒,他还没怎么折腾卢心尧就去了半条命,这叫他如何能够甘心!他就是要卢从景也知道求人是什么滋味!忽然,一声炸雷般的响声。地下室的门被以一种极其暴力的方式打开了,门锁处只能看到熔融的钢铁,还是烧红的颜色,那是极高温度才能做到的。先进来的是几个黑衣的保镖,最后是一个拎着吓得哆哆嗦嗦年轻男人当人形盾牌的英俊男子。“堂哥,好久不见。”卢从景说。卢从景像是扔垃圾似的松开了抓着年轻男人的手,年轻男人跌坐在地上,身上只裹了一件白色睡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嚎,冲着卢承信求救,“爸,救我……”卢从景打了个手势,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年轻男人的头。“安静点。”也就是在那一刻,卢从景看到了卢心尧,瞳孔一缩,几乎失态。他一语不发,视卢承信的人如无物一般,径直走过去割开他手腕的软鞭,不顾一身都是水,把他抱在怀里。他扣住卢心尧的手腕内侧,几乎听不到脉搏了,心跳如同风雨中飘摇的烛火,谁也说不好什么时候会停止。“把手筋、脚筋挑了,就老三套吧,让堂哥看着。”卢从景漠然地说。卢承信霍然起身,喝道:“卢从景,你敢!”“我敢不敢,堂哥应该早就知道的吧?听清了?”手下麻利地掏出短刃挑了那哭嚎不止的年轻男人的的手筋和脚筋,鲜血迸溅,森然阴冷的地下室炸开了浓浓的血腥味,年轻男人惨叫着,在地上扭动着呼痛,嘴里还喊着“痛,痛死了!”。卢从景面不改色,这里太黑了,他干干净净的阿尧不该在这里。“去医院。”卢从景下令,出了地下室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手在抖。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卢从景在这样庞大的家族厮杀博弈,从最初都没有资格被冠以卢姓到后来成为唯一的掌权人,最终得到家主之位,从他十三四岁开始,开枪都不会手抖了。阿尧早产,心肺功能不好,反复呛水真能要了他的命,一想到这个可能,卢从景竟然有点害怕。卢心尧的脸贴着他的风衣,缩起来竟也没多大,衣服湿透了便显出瘦削的身形来,还是个少年人。他又呛了一下,闭着眼睛颤声喊,“……小叔叔。”因为太过虚弱,嘴都没能完全张开,气若游丝。“我在。”卢从景拨开他脸上的湿发,露出白得仿佛透明的那张脸,因为浸了水,洗练出一种干净而单纯的脆弱来,睫羽轻轻颤着。“他说,”卢心尧说得十分艰难,“你要杀我……”说完这话仿佛脱力似的更深地陷在黑色长风衣里,只露出尖俏的下巴。卢从景回答得干脆,低头亲了亲他的额头,“你分明知道。”我爱你。这是他们心照不宣的秘密。卢心尧松松地抓着他的一根手指,突然想起来卢从景已多年不曾这样抱过他,上一次这样抱他的时候,还是在越南的海湾,那时他还只有四岁,好像也是这样千钧一发……没来得及想太多,意识便坠入了无尽的黑暗。而这段非正常关系,自从十八年前,就埋下了种子。意外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