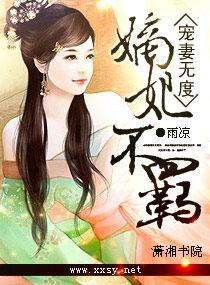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大颜公主福宝 > 第43页(第1页)
第43页(第1页)
“这还用点明吗?”初兰道,“都知这作画讲求虚实、动静、疏密。你画这梅花全无疏密、虚实可言,都是一个模样,这画莫说才俊,只怕是小儿也比不上呢。”林景皓道:“人家作画是求意,臣作画是求实。”初兰娇瞪了她一眼,只道:“那就更不对了,你何时见过梅花这样子的,两两一枝密密挤在一起,一枝不多,一枝不少的。”林景皓正色道:“公主有所不知,在臣的家乡遍山皆是这样的梅花。公主看这两两一枝的花朵,正是一雌一雄,双生并蒂。若是一朵枯萎了,另一朵也是开不了一时三刻便要凋落的,宛如水中鸳鸯,相伴一生,故而又称鸳鸯梅。”初兰原是不信,想林景皓定是哄她,怕不是又要与她说什么甜言蜜语。可见他此刻言辞凿凿,说得真切,却也不像是信口胡说,脸上更是一副不容质疑的神情,心下也没了底气,心道或真有这样的梅花不成?倒也不奇怪,天下之大什么样的新奇事物没有呢?只才这么想着,便见林景皓严肃的神色一转,露了戏谑的笑容,只道:“这花既是一雌一雄的一对夫妻,自然是要黏在一起的,就如公主与臣一般……”他只说着,竟不知何时已揽了初兰的腰,把她圈在了自己怀中。初兰这才发现上了当,娇蛮地锤了他一下,啐道:“没正经,就知道你是变着法的逗趣我。”林景皓笑着握了初兰挥上来的粉拳,在她唇上蜻蜓点水般轻轻一啄,抬头见了初兰的娇美,不由得复又吻上那朱唇。原本的温柔浅吻,在得到初兰的回应后,变得愈加热烈,手也开始不安分的在初兰的腰间揉捏着。“别,这是书房……大白天的……”初兰捏住了林景皓几要探入她衣下的手。然这娇音落在林景皓耳中,却满含了欲迎还拒的挑逗,炙热的吻离了那朱唇,沿着玉颈流下。初兰渐觉身酥骨软,只嘴中呢喃着:“别……景皓……别……”,身子却是无力阻挡林景皓的探取,反而不自觉的去迎合着他的热情。衣衫渐松,初兰微昂着头,胸口春光乍现,美目半闭,低喘吟吟,愈发勾起了林景皓更狂热的欲望。他索性一把将初兰抱坐在了桌案之上,顺势将初兰胸口的衣衫扯得更开些,吻上了去。初兰拥住林景皓,高昂玉颈,只觉身躯似融化了一般,一股强烈的欲望自小腹蔓延开来。亲吻,揉抚,低喘,娇吟,缱绻痴缠渐入佳境。忽地,两下敲门声打断了这几入高潮的缠绵,只听外面画眉带着试探的声音,轻声道:“公主?启禀公主,孙御史和张大人在府外求见。”初兰身子一僵,下意识地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声音。用手推了推林景皓,林景皓正起兴,如何能收得回,热吻密密地落在了初兰的胸口,手则顺着初兰的腿一径向上,探索揉抚着。初兰见推他不开,只略调了气息,回道:“让他们,回吧……”画眉站在门外,虽未亲见屋内是怎样一番情景,却也猜个八九不离十。她才过来时,便隐约听了屋内传来细细的喘息声,这会儿听了公主这声音直个发颤,更是明了了,脸上不由得也是一片娇红。这光景,她这做奴才的本是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打扰的,只眼下这事儿还真非公主出面不行。她只好咽了咽唾沫,壮着胆子道:“回公主,才已经和两位大人说公主不适,不见人了。只两位大人执意不走,还说今日若见不到公主,就在府门口长跪不起。”画眉回了这话,屏息静听里面的动静,却许久未见有回话,只她又不敢再高声打扰,正无措之际,但听屋内传来公主的声音:“带他们到前厅,本宫这就过去。”一盏茶的功夫,前厅。初兰费了好大的劲,在应承了尽快打发走这二人,再好好补偿给他之后,方是挣脱了林景皓的痴缠。这会儿她正站在前厅后的小室,略停了停,作出一副稍显憔悴的表情进了前厅。孙如尘和张墨均为三甲出身,为官多年,身居要职,一为右都御使,一为大理寺卿,素以清廉刚正闻名,在清流儒臣中颇有声望。不用言明,初兰便知他二人此来所为何事。果不其然,二人甫一坐定,便表明了立场,此来正为沈无涯一事。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慷慨激昂,远引圣贤之言,近举前朝之例,直说得唾沫横飞,面红耳赤,大有立时凌然赴死的气魄。初兰只静听,偶尔点头称是,心中却是苦不堪言。一番慷慨陈词后,孙如尘从袖管中抽出一份奏折,恭敬地递了上去,只道:“这份折子乃是臣与张大人执笔撰写的一份折子,在京大小官员近百位在上面签了名,只请公主上奏皇上,还沈大人一个清白,还天下百姓一个公道!”初兰接了这折子细看,不禁一个头两个大,只见这折子竟是洋洋洒洒近万言,措辞亦颇为犀利激烈,初兰心道他们这不是存心送她到母皇那里领死吗!?没想这还不算,只听那张墨开口道:“臣等已经下了决心,如若这封百官联名的折子仍不能打动君心,臣等便去正德殿前跪谏,誓死捍卫公理正道。”初兰忙道:“大人们何必如此呢。”孙如尘道:“公主不必为臣等担忧。为官者,上谏君王,下为百姓,虽死荣焉!”初兰心中直个叫苦,只得讪讪点头,说道:“请二位大人放心,本宫心里有数。”二人见初兰收了折子,只道公主应承了此事,终是如释重负地起身告辞。孙张二人的背影甫一消失,厅后的竹帘便被掀开,林景皓从里面走了出来。初兰知他定是一直隐身于后室静听他们的对话,随手把那份折子递给他。林景皓接过折子,从头到尾扫了一遍,眉梢一挑,不住地点头,语带讽刺地哂笑道:“果真好文采!他们这是怕沈无涯死不了,紧赶着去推他一把啊!”初兰自然明白林景皓的意思,眉头一拧,开口道:“他们真要这么闹下去,只怕掉脑袋的就不止是一个沈无涯了。”林景皓收了笑容,语中不无担忧的道:“公主有什么打算?”初兰叹了口气,愁眉不展,只道:“能有什么打算呢?这可才叫进退两难。这折子我要是递了上去,除了被母皇训斥一顿,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只怕不但救不了沈无涯,反而会激怒母皇,沈无涯自是必死无疑,这些联名的大臣或也要受牵连,只一个煽动皇嗣内斗的罪,他们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林景皓点点头表示赞同,这事儿原只是沈无涯个人的行为,可若是初兰介入,那不管动机如何,就真成了皇嗣内斗了。皇帝自然不容,定会处死沈无涯和带头的几个大臣,以儆效尤。初兰继续说道:“可若是不递,这些大臣们怕也不能甘休。弄不好他们还真敢跑到正德殿那儿死谏,这不又犯了朝堂大忌了?!”林景皓接口道:“朋党之罪,亦是死路一条。”初兰深叹一口气,这些道理他二人讲得明白没用,那些个儒臣们那里却是说不通。虽说他们当中不少人亦是为官多年,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只他们心中尽是公理大义,做事非要分出个是非黑白不可,为此即便是搭进性命却也在所不惜。以前,初兰对他们这种气概,更多的还是敬佩之情。只眼下,初兰却实是叫苦不迭,终是明白了为何同是科举出身,林景皓却总也看不上这些个文人才子,真是怎一个迂腐了得啊。初兰皱着眉头思量了好久,似有了些主意,却也无甚把握,只向林景皓问道:“眼下,或只有一个办法。便是去找大姐,她为人宽容大度,想来应该不会难为沈无涯,亦不会对我生什么嫌隙。让她去向母皇说个情,应该是唯一的办法了。你说,这样可好?”林景皓却是皱眉不语,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他心中有更深的忧虑。他承认这或是眼下唯一可行的办法。若换作是他,他也会有这种选择。不管长公主的宽宏是故意做出给人看的,还是她真有容人之雅量,此事初兰只要开口,没有不成的可能。如今圣旨已下,长公主索讨之封赏均已得到,她犯不着自贬身份和沈无涯一个区区五品小官较劲。她只要开开口,不但卖了初兰一个人情,更成全了她宽大的美名,何乐而不为呢。他所担忧的不是这个办法是否能行得通,而是担心初兰,她虽聪明,亦有筹谋,只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容易相信人了。皇长女,如此特殊敏感的身份,要想在瞬息万变的朝堂争斗中站稳脚跟,并博得众人之赞誉,得尽人心,实非易事,而承容却做到了,这绝不是一个骁勇善战、胸怀坦荡,宽宏大度便能行的。她比那野心勃勃,却只会做表面功夫的尚辰要高明得多。初兰见林景皓这神情,只当他是担心她再落得上次洛飞、陆成一案那样的下场,只笑道:“你放心,大姐不似二姐,她心肠宽厚,没那么多的阴谋算计。我只把话说开了,她自不会多心。”林景皓见初兰一脸率真,更是担忧,开口道:“公主纯善,只把人往好处想。然,人心难测,说句大不敬的话,长公主的宽厚未必不是做给人看的。”他这话原有深意,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借机暗示初兰今后莫太易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