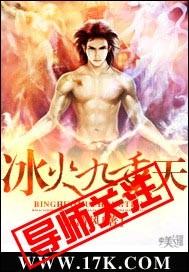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有双链的RNA吗 > 第63章(第1页)
第63章(第1页)
“那个……”余行贴着墙壁飞快看了盛燃一眼,立马把视线移到床尾那团褶皱的被角上上,干巴巴地说道,“谢谢你。”
盛燃也不太自在,就像面对一个陌生人,而他跟这个非典型陌生人又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
“不用,”他叹了口气,“那个人的目标应该也不是你。”
毕竟真正杀死孟宇麟的人是他。
病房又陷入沉寂,明明光明透亮,却又无比沉郁。
盛燃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你这些年过的好吗?”
哪些年?
“还好。”余行随口一句回答,管是哪些年,他这辈子有好过吗?
祁年开口问他:“警察都问你什么了?”
余行抬起头:“就问我事发经过,认不认识他们。”
祁年:“你怎么回答的?”
余行小心地看向盛燃,摇了摇头。
“还说什么了?”祁年语气有些冲,这跟盛燃记忆中的人不大一样,高中时期的年年是个连重话都不会说的温柔男孩儿。
“警察留了我的联系方式,说之后有事会再找我。”余行说,“他们还会找盛燃,等伤情鉴定结果出来,看要不要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没完没了了。
麻药过后伤口突突跳着疼,盛燃难受地闭了闭眼,祁年走过去把床重新摇下去一些,安抚他:“先睡会儿吧,你累了。”
盛燃没力气再说什么,只是看着余行轻轻嗯了一声。
祁年抬起手表看了眼时间,冷冰冰地下逐客令:“看也看过了,你回去吧。”
余行意外地啊了一声:“我……我可以回去?”
“不然呢?”祁年反问他。
“不谈谈赔偿什么的吗?他是因为救我……”
“余行,”祁年不耐烦地打断他,“你赔不起。”
说话间护士开门进来换药,换上新的点滴后也跟着开始赶人:“疫情期间,只能一位家属陪护,你俩……”
“我留下。”祁年说。
余行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开溜,心里乐得像碳酸饮料直冒泡,面上装出一副凝重惋惜的表情,出了门后走路都快飞起来了。一夜没睡实在困,偏偏还有几张设计图等着出稿,回家睡觉都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