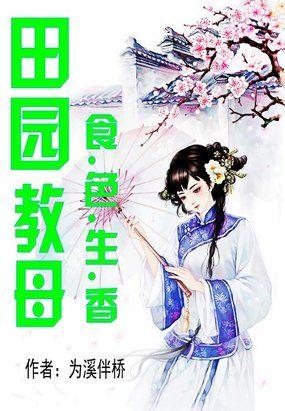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被迫嫁给仇敌以后山楂完整版 > 第112页(第1页)
第112页(第1页)
“因为你的眼神与兰猗甚是相似,俱是不可一世,而本宗主最爱将不可一世之人踩入泥中,好让其肮脏不堪地向本宗主摇尾乞怜。”奚清川舔了舔唇瓣,“嘉徵,本宗主最喜欢你爹爹自裁之时,你看向本宗主的眼神了,愤恨、恐惧、无助,要不是本宗主留着隋华卿与隋琼枝还有用,否则,本宗主当时亦会当着你的面,逼死她们。你的表现一定会令本宗主心满意足。”宁嘉徵气得想打奚清川,却没什么气力。嬴西洲抬掌覆上宁嘉徵的后背,传了宁嘉徵些内息。宁嘉徵回首瞧了一眼嬴西洲,继而抬步走向奚清川,直将其打得鼻青脸肿。穆音从未见过奚清川这副嘴脸,千年来,奚清川完美地将自己伪装成了正人君子,应当登台唱戏,才不浪费这一身装腔作势的好本事。奚清川嗤笑道:“你爹爹死透了,任凭你如何对本宗主不敬,他都回不来了。”宁嘉徵被奚清川戳中了痛处,反唇相讥:“你最爱的兰猗纵然尚未死透,有朝一日,我定会将他送入黄泉。”奚清川闻言,先是不敢置信,接着叹了口气,看宁嘉徵的目光犹如在看目不识丁的无知妇孺,满是无奈与轻蔑,后又用无比亲昵的口吻道:“娘子莫不是撞了邪了?若不是娘子生性淫荡,不守妇道,色诱了穷奇,甚至当着为夫的面与穷奇苟合,勾得穷奇对娘子言听计从,帮着娘子对付为夫,娘子现下早已对为夫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了。兰猗的修为胜过为夫,娘子在兰猗眼中与蝼蚁无异,即便娘子拼了这条性命不要,都不可能伤及兰猗分毫,娘子竟大言不惭地要送兰猗下黄泉。”听奚清川口口声声地唤自己为“娘子”,宁嘉徵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这奚清川分明被自己亲手阉割了,还被自己亲手废了四肢,眼下连站都站不起来,好似一滩烂泥,黏在地上。可是这奚清川的态度竟是高高在上,一如那时对自己生杀予夺的九天玄宗宗主,毫无作为阶下囚的自觉。他自知修为粗浅,经过一番磋磨后,不会再妄自尊大了。但他恨透了奚清川这副面目,且不愿知难而退,定要教奚清川心服口服。1于是他神态坚定,一字一顿地道:“奚清川,我定说到做到。”恍然间,奚清川瞧见了三年前那个在“琼玑盛会”之上,傲慢无礼的小小竖子。宁嘉徵身上那股子的淫靡之气霎时褪得一干二净,变得……居然变得高不可攀,不容亵渎了。千年前的兰猗亦是这副模样,从尸山血海中而来,一身白衣却能滴血不沾,不像是杀人如麻的魔尊,更像是普渡众生的菩萨。他初见兰猗,兰猗正巧杀倦了,连瞥都不瞥他一眼,便翩然而去了。他并未生出劫后余生之感,反而对兰猗着了魔。宁嘉徵觉察到奚清川正在发怔,似乎是透过他,在想些什么陈年旧事。他一把扣住奚清川的脖颈:“兰猗身在何处?”奚清川直直地盯着宁嘉徵:“娘子果真似极了兰猗。”宁嘉徵面无表情地道:“我若是兰猗,三年前,你堪堪闯入重华楼,便已被我碎尸万段了。”他若是兰猗,爹爹便不会被奚清川逼得自裁。他若是兰猗,周伯伯便不会爆体而亡。奚清川温柔似水地道:“娘子若是兰猗,本宗主会更后悔自己太过心软,容娘子守了三年孝,未能在娘子一十又四那年,便破了娘子的处子之身,令娘子汁水横流,淫叫连连。”奚清川所言不堪入耳,尽管宁嘉徵清楚奚清川决计做不到,仍是不免恶寒。宁嘉徵凝了凝神:“兰猗究竟身在何处?”奚清川挑眉道:“娘子若能宽衣解带,服侍为夫,为夫可考虑说与娘子听。”宁嘉徵提醒道:“你切莫忘了自己已是个阉人了。”“阉人又如何?”奚清川憎恨宁嘉徵不识抬举,受着自己的百般宠爱,竟毫不留情地将自己去势,但他面上却堆着笑,“为夫不介意与娘子对食,娘子可用物件捅自己,让为夫饱饱眼福。”宁嘉徵牵了嬴西洲的手:“我已与西洲两情相悦了,何必用假物件。”嬴西洲认为奚清川该当由宁嘉徵处置,故而一直默不作声。纵然他听得怒不可遏,亦拼命忍耐着。宁嘉徵的手指一贴上他的手指,旋即被他紧紧扣住了。奚清川见一人一兽一副浓情蜜意的样子,嘲笑道:“穷奇是上古凶兽,哪里懂什么情情爱爱,待他腻味了,指不定会将你拆骨入腹。”嬴西洲淡淡地道:“吾绝不会将嘉徵拆骨入腹,倒是可以勉为其难地将你拆骨入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