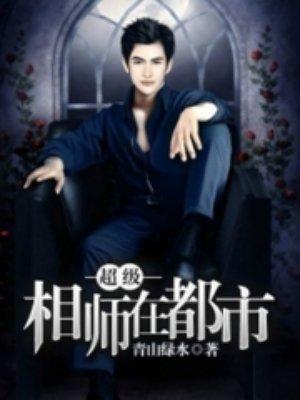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班长总是躲着我番外 > 第85页(第1页)
第85页(第1页)
郭敬眼睛牢牢锁着他,突然道:“你参与了?”许笙深吸口气,默认了。“那你妈呢,她为什么住院?病复发了?”这话问得毫无避讳,许笙隐隐皱起眉,心里竟拨起一股无名的焦灼,纠正道:“她只是疲劳过度,在医院修养几天。”郭敬突然问道:“谁告诉你的?医生?”“不是。”许笙一怔:“是我妈和庄白……”“和庄白书?”郭敬打断他,语气里有些意味深长:“他们告诉你的,你确定不要再确认清楚吗。”许笙眉宇一动,有些怔愣地看着他。“你什么意思?”郭敬的手指触上许笙心脏的位置:“比所有人都要更清楚以后会如何发展的,不是你吗?”许笙心跳猛地一颤,眼里瞬间染上了惊惧的神色,霎那间说不出话来。“班长,别忘了,你现在不是孤身一人,重生的不止你一个。”郭敬贴着他的耳边,低声道:“你现在放弃就太早了。”许笙大脑混作一团,那人的声音却一字一句地传入耳侧,清晰如丝。“你要像上辈子那么窝囊到死吗?嗯?许笙,你想那样吗?”郭敬揉了揉被他握的发红的手腕,盯着他发颤的耳廓,轻声道:“离开庄白书吧。”许笙在原地站了许久,反应过来时,手指还在隐隐发颤。郭敬已经走了,两侧人来人往,却没人能注意到那个在病房门口直愣地站着,被压抑和惊惧一点点笼罩的青年。许笙不明白郭敬那些话的意义,也不知道那人抱着什么目的,可他心里很清楚,郭敬只是揭开了他一直欺骗着自己的表壳,挖出来他一直逃避、不敢遥想的事实,字字诛心,针针见血。但没确认之前,他做不了任何决定,也没有余力去伤害任何一个他爱的人。这个点快到李主任下班的时间,许笙匆匆下了楼,几步道走的浑浑噩噩,等进了诊室,发现人家都换上了平时的便装,果然要下班了。“大夫。”老大爷闻声一瞧,就看到表情不大对劲儿的许笙,之前复查了几次,他认得这个年轻人,问:“有事儿吗?小伙子。”“打扰了,我想跟您确认一些事。”许笙喉结鼓动着,湿润的手心冰凉一片,他听着自己的声音缓缓道:“关于我妈的病情。”大夫愣了一下,往脖子上挂围巾的动作也跟着一顿,他看向许笙,道:“你想确认什么?”“我想知道,我妈那天到底因为什么被送来医院。”许笙发现他越往下问,那股莫名的恐惧就往上升腾一分:“…她真的是疲劳过度吗?”“……”老大爷抬头看着他,脸上的表情既不是肯定也不是怔愣,而是仿佛手术失败要告知亲属时,那种短暂压抑着的沉意和默然。许笙感觉心头发紧,牵动着每一条神经都被绷紧了,竟有种等待审判般的难受。“你的母亲是这么告诉你的?”“……是。”许笙攥紧了拳头,他这么问就代表其中一定不寻常,那个无法逃避真相也似乎离他越来越近,他哑声道:“难道不是吗?”“嗯。”老大爷深深的法令纹把脸部线条勾勒地愈发凝重,他把那时告诉庄白书的情况,一五一十地重复了一遍:“你的母亲四年前曾患了乳腺癌,当时把左侧整个乳-房切除,可以说是基本治愈了的。”许笙无言地听着,心越来越沉到谷底。“但她昏倒的当晚,我们给她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她的乳腺癌复发,并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胸椎。”“她的病……复发了?”“是,她不告诉你大概是因为你还在上学,怕你担心,怕耽误了你的前程。”老大爷扶了扶眼睛,语重心长道:“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知情,毕竟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作为男人,你应该担当起你的家庭,别让你妈一个人承受那些。”许笙像是丧失了思考能力一般,麻木地看着老大爷的嘴一张一合,全身如坠入了冰窟,冷得没剩一丝温度。“况且她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必须立刻住院配合治疗,不能再拖下去。”……许笙也不知道自己后来说了什么,又是怎么跟大夫告的别,当他走出了那条灯线白晃的走廊,只觉眼前发黑,阴翳遮住了他昏胀的视线,催剧着他发烫的眼阔。他不知道用了多久才消化掉这个消息,尽管他早有预感,却把这颗□□埋在了最深处,好像把倒计时的声音隐埋住,就不会爆炸一样。癌症,复发。这几个字不仅是一个通知,一个宣判,更像一把重锤,仅仅一下就敲碎了他所有仅剩的理智和可笑的妄想。现在的他,如一具行尸走肉,他没有任何时候要比现在迷茫,他甚至不知道该去哪儿,明天要干什么,他还剩下什么理由活下去。他甚至不想待在这个医院,因为他更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徐梅,怎么面对庄白书,他现在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睡一觉,他既不能死,又没能力改变未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看着他是怎么变回一个人,他也想不通,为什么只有他,要一次又一次经历这种痛苦?他只是个普通人,任何一件作奸犯科、大逆不道的事儿他从没做过,他只是出生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幸运的遇到了一位想相伴一生的恋人,为什么把这一切都毁了之后,又给他机会,却又让他绝望?他做错了什么?许笙出了医院,天色已经彻底暗下来,市中心最繁华的夜景在霓虹灯耀的光亮中熠熠动人,正值深冬,许笙身上却只穿了间薄衫,他伸手拦了辆车,上车报了目的地的名字。司机看他这身打扮和面如死灰的神色,还恰巧是从医院里出来,还真怕这位是个神经病,再不就是家里死了人,一路上也没敢跟他交谈。车里的广播塞满了整个狭小的空间,许笙好一会儿才知道,今天原来是元旦。车停下时,司机报了数,许笙掏了掏兜,庆幸自己身上带了些零钱,他浑浑噩噩地下了车,抬头望向一排排高耸的建筑,尽管黑了天,周边的绿化和彩灯却把小区映得通亮。他好久没来这儿了,上辈子这里是两个人的家,这辈子变成了他们假期约会的地点,这里曾是他熬过孤独时最绝望的空间,却也装载了他最无法忘怀、甜蜜的能回味上一辈子的记忆。恍然间就好像回到了那时候,他先是在楼下的店铺里买了够他喝上一晚上的酒,然后拎着大瓶小罐上了楼。钥匙一转动锁口,大门应声开启,屋里漆黑一片,暖气却给的很足,屋内工整洁净,一看就是经常有人来打扫。许笙换了拖鞋,把酒瓶放到了沙发旁的玻璃桌上,他很久没有这样,不经人打扰地独处,就好像真的只剩下了他自己,没人再逼着他去改变什么,他也没剩什么可以失去,他不用再害怕了。许笙启开了酒瓶,一口一口地开始灌,他平时若不是必需也从来不碰,到了这时候,酒反而成了好东西,他在自己家里喝,也碍不着任何人,他可以褪去所有的伪装,卸掉一切的枷锁。此刻,他不是任何人的依靠,也不用背负任何使命,不用去拯救任何人,他就只是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没能力照顾好母亲的儿子,他可以尽情地悲痛自己的失去,后悔自己的不周和无力,发泄出这场突如其来、彻底改变了他生活的事故以来积攒的痛苦。手机在玻璃面上响动了好几次,嗞嗞的振动声弄得许笙一阵心烦,他把手机调成静音,翻了个面,扣在桌子上。屋内又安静下来。许笙又灌了口酒,整个过程没有下酒菜,也没有人在旁边做伴,甚至连点光亮都没有,只有一味地闷头喝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