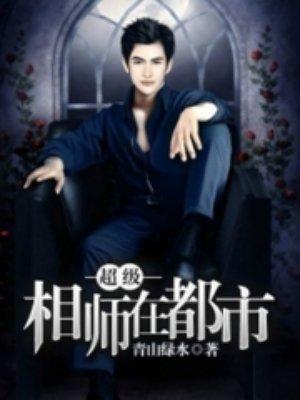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艾德里安txt结局 > 第25页(第1页)
第25页(第1页)
看着那些大小不一的茶色药瓶,安德烈随了上去。停下,护士为病人分发药片和水,叮嘱他们用药后,再推车向前。“你好。”尾随一段时间,安德烈决意上前。护士转过身,仰头注视安德烈。“你好,需要什么吗?”“是的……可否给我些消炎和退烧药?”安德烈瞥向推车上的药瓶。“我的朋友受伤了,还有些低烧。”“什么时候受的伤?严重吗?”安德烈不想说太多。“……几天前,只是用酒和食盐水简单处理过伤口。”护士皱眉,说:“你或许应该带他过来,让医生看看。”“好,不过先给我些药和绷带应急吧……”“等一下。”看她消失在一扇半掩的门后,安德烈抿嘴,抱起臂膀,倚靠在一旁的病床床尾。病床上的患者,懒懒地睥睨他。“德尼老爹,我说了几次了,你不能吐在这里!”忽然,某处响起了一个尖锐的女声。角落里,一位老年人正扶住墙壁呕吐。放下病历夹,女护士皱眉走了过去,对他一阵奚落。“如果你想吐,就举手告诉我们,这都记不住吗?!”老人靠墙坐下,灰白的胡子上沾满秽物。护士掩鼻,嫌弃地后退几步。“天,这肯定是霍乱。”她小声嘀咕,又说:“我真是受够了这个地方!”“德尼,你还好吗?”一个人影,小跑到老人身旁,摸摸他的额头,又掏出手帕为他抹擦嘴角。“别担心,等下我会清理干净的。”将帕巾掖回口袋,那人尝试搀起老人。“里昂……她说的没错,这是传染病……你也离我远点吧。”老人唉声叹气道。里昂?“这瓶是感冒药,镇痛退烧。另外这个是磺胺粉,撒在伤口上消炎。”正诧异里昂也在这里,取药的护士回来了,她手拿两瓶药和一卷绷带,并向安德烈大致说了一下用药方法。“试试吧,如果症状没减轻,就把病人……”叮咛道,却见安德烈的注意力在别处。“你有在听我说话吗?先生。”“好,我知道了,谢谢你。”“最近都是些上吐下泻的病人。”顺安德烈的视线望去,护士叹气,她将药塞给安德烈,边说:“……但愿你朋友得的不是败血病,那就需要盘尼西林,整个北部地区连一支盘尼西林都没有了。”老人捂住腹部,随同里昂走一拐一瘸地向了病床,他重重地躺倒在床上,如释负重。低伏在他的耳旁,里昂又说些了安抚的话。“……只能眼睁睁看病人死去,真是让人感到伤感。”说完,她推起换药车,继续去忙了。安德烈握紧了手里的药物。为德尼盖上被子,里昂抬头,注意到了安德烈。安德烈转身,走向礼堂大门。“安德烈!”里昂跟了上去。那高峻的背脊迟疑后,才转回身,与他寒暄。“里昂,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红十字会的人允许我在这里过夜,但我要帮忙看护病患。”“看来你找到了可以暂时安身的地方,祝贺你。”笑笑,里昂看向安德烈手里,问:“‘ibuprofen’和磺胺粉?安德烈,你生病了吗?”“……嗯,施工的时候受了点轻伤,没什么事。”随意找了个理由搪塞。忽然,里昂靠前,伸手摸上了安德烈的前额。略略碰触到,安德烈及时躲避开来。“我说了没事,你继续忙吧。”安德烈显得很烦闷,没再给里昂说话的机会,扭头走远了。凝看那轮背影,里昂低垂眼睑,喃喃:“安德烈……”他攥攥手,再张开,看着掌心斑驳的纹路,感受那抹余温。败露“珍。”备药室里,叫珍的护士正手握注射器,用针头抽取药物。“打扰你一下……刚才向你借药的那个男人,他生病了吗?”反感被打断,珍攒攒眉头。“不是噢,里昂。”索性放下针筒,珍回答说:“是他的朋友。”路经西城区时,一群人正在排队汲水,他们往井里撒下粉末状的明巩,谈论最近在坦卡特爆发的疫情,忧心忡忡。观望片刻,安德烈上前,与队伍的前侧佝偻着腰背摇晃绞轮的老妪攀谈了起来。说着说着,老人家堆起满脸笑容,接过辘轳,安德烈将推车上的水桶灌满了。推到一旁,安德烈俯下身,掬水饮了起来。他像是渴坏了,水淋湿前襟。喝得差不多了,安德烈抬胳膊擦擦嘴,与老妪道别。看到,里昂跟随上去。继续往北走去,末了,安德烈停在一间店铺门口。透过橱窗,里昂看到安德烈在货架间走动,随意挑选了些食品,很快便又出来了。就这样,他们一前一后,越走越北,日光悄悄偏斜,拖落出斜长的影子。里昂也越想越多。果真,他还是很在意。明明不是一个人,安德烈为什么要欺骗他呢?他又不是那种不识趣的人。待回过神,里昂才发觉自己一路跟踪到了市郊。路上已没有什么行人,蔽体的建筑物愈来愈少,他有些忐忑,于是放轻慢脚步,尽量拉远距离。直至离开了城区。看过去,那是一条一眼望不见头的泥石道,道旁栽种有魁大的法国梧桐,斑白的枝桠抽芽吐绿,满满的翠色,风来,整个树林都活动了起来。安德烈独走在这成排的梧桐树之间,渐渐地,化成一个灰白的小点。里昂迟疑了。彼处披霞,色彩浓抹,周遭很快就要沦入黑夜。他这样看起来,十分地愚蠢可笑吧?即便安德烈有意欺骗、隐瞒,他又能过问什么呢?正犹豫,前方,安德烈忽然停住,转向了右侧。眼看他即将消失在岔道上,里昂来不及再多想什么,咬咬牙,跟了上去。“……安德烈。”门被推开,又阖上。安德烈抬眼,看见艾德里安依然清醒着。没有过多的对望,他穿过客厅,将牛皮纸袋摆放在流理台上。焦色的法棍面包露出一小截,艾德里安却提不起一丝一毫的食欲。“还好吧?”走近,低睑看看桶内,里面空无一物。将它踢到一旁,安德烈俯下身,注视着艾德里安问道。“没喝水吗?”“没。”“我拿回两瓶药,一个消炎,一个退烧。”摸出药瓶,一瓶摆在茶几上,一瓶安德烈拧开,取下棉塞,倒了三粒在掌心。“来,吃下去。”托住艾德里安的颈后,将他扶起。捻住药片,艾德里安放在嘴里硬咽了下去。干咽药片可不好受,反倒起了催吐的效果。“如果吐了,就再吃。”“……”“你会好起来的。”安德烈伸出手,抚抓艾德里安的头发、耳郭与脖颈,依然是那湿湿烫烫的触感。光线愈加黯淡,黑暗迫近,注定了是个难熬之夜。可怜的艾德里安。躲在窗后,里昂屏住了呼吸。那抹金发,惹眼又令人厌畏,是他长达数年的梦魇。安德烈抚摸它,指缝与发丝交葛、缠绕。艾德里安轻眯起双眼。他难以置信、也无法理解……后退,脚跟出了矮阶,一趄趔,重重地跌倒。“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墙根的瓦盆碎了,沾上一手的黏土。“谁?!”闻声,安德烈警觉,几步走到门前。挣扎站起,里昂顾及不了太多,踉跄逃跑。翻出栅栏,踩到裸石上湿滑的地衣,近乎连滚带爬下了缓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