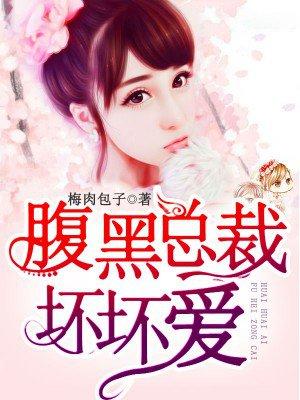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道媛百度百科 > 第63页(第2页)
第63页(第2页)
“说了你肯走?”
文无隅眸光霍地凌锐,谢晚成连忙收敛了笑正色以对,话出口却是,“还是你懂我,反正我不会走的。”
文无隅摇头叹一记,一山更比一山高,谢晚成比他还赖得厉害。
谢晚成见他脸色缓和几分,便知他拿自己没法,索性抱了手靠墙,耐心等候文无隅权衡出个结果来。
“之所以说此行凶多吉少,是因为这其中极有可能暗布陷阱。”文无隅思量再三,最终将疑虑道出,“怕是这次行动有去无回。”
谢晚成不解道,“怎么说?”
“王爷向来谨慎,一开始就不相信吾是来自娄瀛山师承白云观,今次出游或只是障眼法,目的是引吾等自投罗网。”
“你肯定他已经知道你的身份来历?”
“不敢肯定。”
“你,还是他?”
文无隅迟顿了一下,“我。”
谢晚成挠挠脸颊,做出个百思不得解的表情,
“这么说的话你不觉得很矛盾吗?他若肯定你是文家后人,接近他必是找他寻仇,为何还留你在身边,这一年多来他陪你演戏的目的又何在,早早将你揭穿省去多少麻烦,何苦玩什么欲擒故纵。只有一点解释,那就是他动了情,”
谢晚成口气斩钉截铁,可这句说完连自己都不信,指节摁得咔咔作响,“倘若真如此,他更该将功抵过让你们一家团聚了…不懂…”
文无隅一直垂首默立,他又何尝不想知道,王爷葫芦里到底哪一味才是真药。
好一会儿他恍然,不由地冷笑,“王爷心思精绝,那么容易被猜透,他如何在皇权重压之下泰然高卧,有件事一直没机会告诉你,当年宰相渊尚徽之死,和钟氏皇帝脱不了干系,王爷恐怕早就参透。”
谢晚成惊愕,空张着一张嘴说不出话来——认贼作父为虎作伥,隐而不发十多余年,此等定力他自认远不能及。
文无隅见他神思远飘,又道,“无关之事就别多想了,总之做最坏的打算不会错,一旦发现异常,立即撤散。”
谢晚成正色道,“若是不幸被你言中,要想再次劫狱可就难了,你有后续计划吗?”
文无隅躲开目光,垂眼看地,“只有摊牌一条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抵死不认终究不是万能的。
谢晚成忽地一下闪到他面前,“你这个人就是想得太多,太过,要我说与其瞻前顾后,不如殊死一搏!再者,他现在不过顶着王爷的虚衔,能动用的侍卫有限,我就不信他无所顾忌,动静闹大了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好事。”
文无隅闻言灵光一闪,终于长舒一口气。谢晚成说对了要点——藏匿逆党,罪比通敌!王爷当然有所忌惮!
“师兄言之有理!”
“我这就去放信号,让他们天黑进城。”
谢晚成急着要走,却被叫了住,
“还有一事,吾若料之不错,那么曲大人今早便是同王爷见面,来回大约两个时辰,王爷欲使请君入瓮这招,不会让他加强戒防,且也一定出了城,你们至多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谢晚成拿眼翻他,“说来说去又绕回来了,你的疑心也很重啊!姑且算你想的都对,可也势在必行了不是吗,凭我和赫平章,半个时辰都嫌多,你宽心吧。”
房门启而复合,明暗分两边。
浮云悠悠然蔽日,天际风起,贯四海十方。
幽灵兰蹁跹起舞,如同鬼魅猖獗于白昼。
棚亭下,一人躺卧在藤编摇椅里,以书盖脸,足尖一下一下轻点地面。
一个人影悄然靠近,有心捉弄摇椅里的人,他蹑手蹑脚地绕到摇椅背后,俯下身,朝那人耳边大叫了一声。
谁知那人不带抖一下,毫无反应,他立马换了个丧气模样,坐到旁边藤椅上,抬手一把掀翻了书册。
露出的那张脸不是怀敬王渊澄还能是谁,一双雪亮的眸子空空荡荡,不知盯着哪里只几不可闻地落了一声,“幼稚。”
这话说的正是‘童心未泯没心没肺’的曲同音。
“我爹出府去了?”
曲同音路过大堂内院,没见摆花弄草的身影,随口一问。
不过没人回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