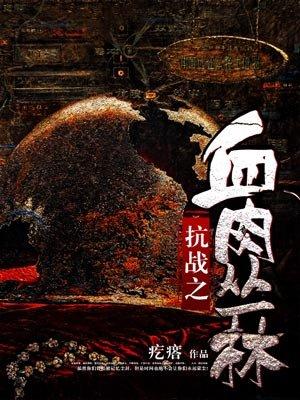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偷生番外虾磕续命诸戈 > 第88页(第1页)
第88页(第1页)
“让你见蒲英?”安柏微慢吞吞地重复了一遍。
“对、对……蒲英。”万昌廷作为一个学者的冷静和沉稳尽数褪去,露出表壳下状如婴孩的拘谨和紧张。
“你就没有想过,蒲英已经不在的事实吗?”安柏微一字一顿,“你知道我进火场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吗?那个才十七岁的男孩趴在你身上,他身上的衣服都在燃烧,头发也烧着了,但他依旧保护着你,哪怕被烧成那样,他也没有往旁边偏离半分。”
万昌廷的胸膛剧烈起伏了几下,像是即将要大哭起来似的,可是他没有,他用最后一点尊严压抑住了眼泪,尽力维持着声音的平静:“蒲英不可能不在,他一定还在。”
安柏微怜悯地看了他一眼:“如果他还在,为什么不来看你?万教授,您难道从来没有想象过没有蒲英的生活吗?难道蒲英必须时时刻刻都待在你身边为你做事吗?或许他爱的卑微,但您不该把他想的也如此卑微。”
“我没有……”万昌廷无意识地摇着头,他还想张嘴说些什么,却蓦地失了声,接着一把捂住脸,眼泪登时流到了下巴。
杨乐佩轻轻叹了口气,他看了安柏微一眼,扑面而来的是无比的熟悉感——安柏微总是有这种能力,几句话就能戳中人心最柔软地方的能力。
“如果您非要一个说法的话,我可以明确地告诉您,蒲英已经不在了——不是别人,就是您的儿子,您的爱人,万蒲英,他已经不在了。”安柏微平静地说,“他死于您亲手放的那场大火,也死于为了将您从火中救出,他的生命始终是在为你流逝的,他的死,你怨不得任何人。”
万昌廷说不出话,巨大的悲伤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他的喉咙,使他连呼吸都困难起来。
“您刚才说,有些事,需要用大火来纪念,您什么都不要了,只要蒲英。”安柏微淡淡道,“如果您想让蒲英安息的话,希望您能把今年做过的事坦白交代,好让蒲英离开的有些价值,而不是不明不白地被自己的爸爸亲手埋葬。”
……
从万昌廷的病房出来后,安柏微长出了口气,把那些负面情绪统统排出体外,随后朝杨乐佩晃了晃手里的录音笔,有些疲惫道:“让小文把他的口供整理出来,等他痊愈后交给俞风处理接下来的事情,我估计可能是无期或死刑,看在他态度还算诚恳的份上,不知道能不能判成有期……看命吧。”
杨乐佩意外地没有插科打诨,默默接过录音笔后,抬起红得像小兔子似的眼来,轻声问:“蒲英真的死了?”
“我也不知道。”安柏微揉了揉他的头发,低声说,“医生说,命是保住了,但蒲英到底能不能醒来,就不知道了。我找个合适的机会,让万昌廷在吃牢饭之前再陪蒲英一段时间吧,那小家伙万一做了噩梦,身边有万昌廷陪着,估计也不会太害怕……别哭了,三十多的人了,丢不丢人?”
“我只是觉得那小孩特别招人疼。”杨乐佩的小脸皱成一团,鼻头也红红的,“你说说,一个十七岁的男孩,感情怎么会这么细腻……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僵硬木讷的爹……”
安柏微轻轻摇头:“有些感情,谁也说不清怎么就产生了。万昌廷要是愿意多分点精力在蒲英身上,估计也不会发生今天的惨剧……说来说去,还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太不平等了,蒲英爱的畏手畏脚,卑微又可怜,万昌廷则强夺豪取,丝毫不知体谅,稍微表现出一点爱意就把蒲英迷得死去活来……万昌廷最后倒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只不过他醒悟的实在太晚了,蒲英终究还是没等到一份完完整整的爱。”
“你别说了。”杨乐佩擦了擦眼角的泪,低声喃喃,“你说的我又想哭了。”
安柏微叹了口气:“其实哪里有绝对平等的爱?能够经营好、维持好已是不易。”
“所以你和陆辙谁更爱谁多一点呢?”杨乐佩擦着眼泪,又忍不住八卦地问道。
提到这个问题,安柏微稍稍抿了下嘴,有些惆怅地笑了:“你看我对那小崽子这么上心,时时刻刻都想黏着他,但实际上他也是个心思细腻的人,要真是说起来,我反而觉得小辙是多爱一点的那个,只不过他不善于表现,别人也轻易察觉不到……如果不是他爱我,我根本没机会跟他在一起,你看蓝绍齐和江朔,陆辙看他们的眼神跟看我的根本不一样,但他自己从来不会主动说出来。”
杨乐佩:“……”
他觉得自己不该问这个问题,多嘴多的直接把狗粮吃饱了。
“没什么事我就去照顾陆辙了。”安柏微突然欺身上来,抱住杨乐佩的脑袋一通狠揉,后者还发着懵,安柏微已经扬长而去,他一头雾水,不知道安柏微刚才发什么疯,扭头想往回走,却看见祁修拎着盒饭站在不远处看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