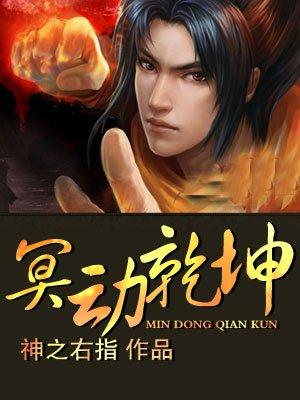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红色痉挛 > 第100章(第1页)
第100章(第1页)
投影屏上始终没出现与赵卫东有亲密记忆关系的画面。因为他家当年住在县城边儿,县文史资料馆没保存那一条小街的老照片。
灯亮了。窗帘拉开了。
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都流淌着泪水,只有赵卫东显得异常平静。
他问:&ldo;我们的家乡现在还是那样吗?&rdo;
乔博士告诉他,呈现在投影屏上的全都是三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年代的照片。如今,那县城肯定已经旧貌换新颜了。变化究竟有多大,到时候他们最有发言权……
&ldo;什么时候?&rdo;
&ldo;你们回去的时候啊!&rdo;
&ldo;我们怎么回去?&rdo;
&ldo;由民政系统的同志陪你们回去。我们对你们的责任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还剩下一部分经费,不但够你们回家乡,还够你们全国各地观光一番。那笔钱,是社会各界关爱你们的人为你们捐的。我们都认为我们一分钱也不能截留,都应该属于你们。&rdo;
&ldo;老院长&rdo;回答得由衷、坦荡而又光明磊落。
赵卫东仍问:&ldo;还有一个问题,也许是我所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是不是一旦把我们送回去,就让我们待在那儿了,不再管我们的什么事儿了?&rdo;
&ldo;老院长&rdo;沉吟了一下,低声反问:&ldo;你指的是哪些事呢?&rdo;
而李建国按捺不住地嚷道:&ldo;这算问的什么!先回答我的问题‐‐我父母如今活得怎么样了?&rdo;
肖冬梅立刻表态:&ldo;同意!这也正是我想首先知道的!&rdo;说罢,回头问姐姐:&ldo;是吧姐?&rdo;
&ldo;老院长&rdo;也似乎不想正面回答赵卫东的话。起码是不打算在当时的情况之下立即正面回答。从乔博士告诉他当年的红卫兵们的家乡找到了以后,欣慰之余,他内心便继而替他们感到忧伤了。而乔博士接着向他汇报的情况,使他的心里又开始承受着一种压力了。联欢会是他主张举行的。他希望通过欢乐的气氛冲淡必将接踵而来的大悲哀。现在他意识到他对联欢会的效果预期过高了。
他将暗示的目光望向了乔博士。
于是乔博士说:&ldo;那么,就由我来宣布关于你们的父母们的情况吧。我是不情愿用&lso;宣布&rso;这一词的。因为听起来仿佛冷冰冰的。而我一时又想不到另外一个更适当的词。事实上,这是我所充当的最有难度的角色。我却一筹莫展,只有向你们读这一页从你们的家乡电传来的纸上的文字。这上面是这样写的:
&ldo;李建国‐‐父亲在1970年,因不堪忍受莫须有之政治罪名下的迫害,自杀身亡。母亲于1984年病故于县民政局办的养老院。哥哥李建宇,现任县电力局局长。
&ldo;肖冬云、肖冬梅‐‐父亲在1971年,因不堪忍受反复批斗和人格凌辱,精神分裂,长年沦落街头,死于
车祸。母亲今尚在世,收住于县民政局办的养老院,但已于多年前患老年痴呆症。经认真访寻,认为二姐妹在本县已无直系亲人。
&ldo;赵卫东‐‐父病故于1986年;次年母亲病故。一姐一弟仍在本县。姐目前失业在家;弟以摆摊为生。
&ldo;……&rdo;
乔博士读罢,室内寂静异常。
他又说:&ldo;由我来读这页纸,我感到十分遗憾。但我觉得,仍有必要告诉你们这样一点:你们家乡的有关部门,为协助我们了解你们的父母及亲人现在的情况,做了大量细致的访询工作。他们对他们所提供的情况的准确性,是郑重地做了保证的……&rdo;
突然地,肖冬云、肖冬梅几乎同时放声恸哭。
紧接着李建国也爸呀妈呀地哀号起来。
&ldo;老院长&rdo;没劝他们谁。他不知该怎么劝。他默默地离开了会议室。
另外几位&ldo;核心&rdo;人物也垂下目光相继离去。
乔博士走到肖冬云身旁,将一只手轻轻按在她肩上,真挚地劝道:&ldo;三十几年了,人世沧桑,节哀吧,啊。当姐姐的,得比妹妹刚强些,对不?&rdo;
见肖冬云一边哭一边点了下头,他也离去了。
只有赵卫东没哭。甚至,也没流泪。他两眼定定地望着雪白的投影屏,仿佛是瞎子,什么都不曾看到过;仿佛是聋子,什么都不曾听到过;也仿佛是哑巴,什么都不曾问过;还仿佛仍是一个失忆人,什么都不曾回想起来。
然而,进入会议室以后,拿在他手里的一个又大又圆的橘子,确乎是被他攥扁了。橘汁顺着他的指缝,一滴又一滴,无声地滴落在红色的地毯上……
那一时刻,他内心究竟想些什么,没人能比较清楚地知道。因为他不曾说过。那成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
四名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开始了在全中国各大城市的旅游观光。他们最先到达的是天津。在天津逗留了两天,乘一辆中巴沿高速公路到达北京。北京是他们的一个梦。天安门广场曾是他们的精神圣地。曾是他们一心朝拜的红色的&ldo;耶路撒冷&rdo;。他们在北京观光了一个星期。故宫、颐和园、圆明园、香山、
长城,总之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对于他们,北京少了一道他们最为熟知的革命风景。那就是天安门城楼对面,广场两侧&ldo;马恩列斯&rdo;的巨幅画像,和那句一百年来影响世界的著名口号标语‐‐&ldo;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rdo;这使他们都不免觉得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有些孤独。在他们心目中,&ldo;马恩列斯&rdo;的画像,以及那口号标语,以及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同组成着首都北京的标志。但对于他们,北京也多了些新的事物。首先自然便是毛主席纪念堂。陪行的民政部门的同志,安排他们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其次便是一幢幢目不暇接的摩天大厦。他们还在某娱乐城看了一场俄罗斯风情的舞蹈演出。而开演后才知道并非他们以为的什么民族舞蹈,而是几乎全裸的高大又苗条的前苏美女们的艳舞。不过并不低俗。追灯摇曳,红光紫气,流霞溢彩。美女们的艳舞热烈、神秘,
性感、魅力四射迷幻旖旎。两名陪看的民政部门的同志顿觉不安,认为带他们看这类演出是自己们犯的一个严重错误。交头接耳讨论了半天,打算带他们离去。最后统一了态度,决定顺其自然,既来之,则安之,何必太过自责。这一决定显然是明智的。因为四名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一个个看得目不转睛,如醉如痴。比周围观众鼓掌鼓得更起劲儿。此种情况之下硬将他们拖拽走,似乎也太缺乏理解了……
在工人体育场,两名带队者陪他们看了一位内地当红女歌星的专场演唱。肖冬云得知每张票要200元,主张不要看了。她不便说票价贵,只说自己们不能太奢侈,什么都看。而两名带队者笑了,告诉他们其实也不算贵。说要是想到了下岗工人自然就会觉得奢侈。又说有时候最好就别去想。说前两年,一名是歌星的台湾小女子来北京举行专场演出,头等票价高达2000元哪!而连演三场,场场爆满,总共售出了六万多张票。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直听得瞠目结舌,如听外星之事。缓过神来以后,接票时也就心安理得天经地义了。从此口中再未说过&ldo;奢侈&rdo;二字。赵卫东对两名带队者一路上的一切安排,都持没有态度的态度。仿佛是一位哑巴君王。仿佛一切高级的待遇,对自己而言,都谈不上什么奢侈或不奢侈。都是不必庸人自扰的事。享受没商量。而在两名带队者方面,不但相互之间每每意见相左,各自内心里也常常矛盾。他们既希望使赵卫东们多看看三十几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多了解多接触三十几年来尤其近几年来的新事物,又顾虑不少,怕在自己们的安排之下,使赵卫东们看到了不该看到的,接触和了解了不该接触不该了解的。赵卫东在四人中年龄大两岁,他们自然就将他对待为四人中的代表人物,委决不下之时,自然也要首先征求他的意见。而他似乎早已有了一定之规,以没有态度的态度相应付。如果说,在&ldo;疗养院&rdo;里,他还很在乎他在四人中的代表资格和特殊地位是否如三十几年前一样巩固,一样不可取代,并且更在乎是否被悄悄篡权了;那么自从离开&ldo;疗养院&rdo;那一天起,他显然已决心彻底放弃自己在四人中的代表资格和特殊地位了。他做这一决定究竟又是缘于怎样的想法,也没有任何人清楚。只有一点,肖冬云姐妹和李建国还有两名带队者是看出来了的‐‐他那样对他是绝对有好处的。因为他只要心安理得充聋作哑地接受别人的周到安排和服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