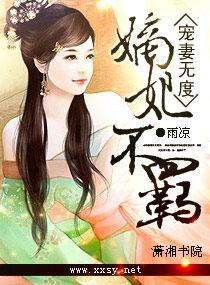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时晓晚来天欲雪 > 第21节(第3页)
第21节(第3页)
便是他的叔父,不久前虽回了青州,然这厢打听贺兰泽如何安置谢氏女的书信已经送来他手里……
从李廷掌事到医馆首领,原都只为一人掌舌。
“薛大夫如此看着老夫作甚?”
薛灵枢闻言便收回目光,叹了口气,“李掌事不若看看,这夫人眼下居于何处?”
以画师身份入的府,没有另辟院子,就住在贺兰泽寝殿的偏阁中。
薛灵枢没再理会愣在一处往二楼眺望的人,只摇着扇子继续往前走去。心中感慨,要不是贺兰泽自个还要糊层面子在脸上,估计偏阁都省下,直接将人置在他寝殿了。
这样一想,他不由也顿下足,回首看了眼李掌事。
贺兰泽是知晓此人乃其母之人,但为了不让母亲挑上的女郎们入府侍奉,便容这人留下,亦算一场博弈维持着无形的平衡。
然而眼下如此堂而皇之地带回了谢氏女,局面就此失衡……
薛灵枢抬眸看漫天春光,只觉背脊发凉,山雨欲来。
果然,前院的议事堂中,亦如薛灵枢所料。根本无需青州城中的老夫人施压,原本冀州城中的文官武将便已经开始话里话外表达不满。
他们自不在乎主上私事,但是以州府之兵施压一处烟花地,抢夺一个风月女,实在不是什么明德之举。
文官恐损主上私德,武将担忧和幽州城的联盟。
薛灵枢侯在外头,直近午膳时候,也不知最后贺兰泽作了何样安抚和承诺,属臣们方三三两两出来,观面色也不尽好看,依旧忧心忡忡。
反倒是贺兰泽翻阅他送来的脉案,眉眼比起前两日,明显疏朗温润许多。
“夫人根基薄弱,多半是久病阳虚、气不归元所致。不是大病,慢慢养着补回气血就好。”薛灵枢专注自己分内事,遂摇着扇子道,“但您瞧这脉案,她近来心忧急惧,脉象越来越乱,心病且需心药医。”
“孤明白!”贺兰泽合上按脉,“多来牵挂那个孩子。”
“所以呢?”薛灵枢闻言问道。
“孤给养着,还能如何!”贺兰泽合上按脉,眼前蓦然又浮现出皑皑的模样,只垂眸笑了笑,“不过,孤也得要个自己的孩子。”
薛灵枢摇扇的手僵在一处,“和……她?”
贺兰泽剜他一眼,尤觉他多此一问。
“这些年无论是阿母还是属臣官员,不总是拿孤无有后嗣说事吗?如今且成全他们,两厢欢喜!”
母以子贵。
薛灵枢回过味来。
“可是若如此,又是一场博弈,压力便全在了您和夫人这处。如何不考虑先做通这处事宜?尤其是老夫人处,何不先得了她的应许,至少且把与公孙氏的婚退了……”
薛灵枢拢住扇子,蹙眉道,“如今这样是否太急了?还不若寻处地方,将夫人先安置起来,实在担心各处眼线,您可以用我的府邸或医馆,也不妨碍你们见面!”
“不可!无论是说服阿母还是依礼退婚,都不是日能成的事。将她置在外头,更是犹如外室。她本就心思重,又历了灭族之祸,满脑子想得愈发多。说到底,孤要娶她,怎么都要过阿母那处,与其畏畏缩缩将她藏着掖着,让阿母以为孤尚有顾虑,不若索性摊明了。她出身谢氏,纵是家族覆灭,骨子里的东西不会丢,这点面对困厄的勇气自是有的。”
“是故眼下直接一刀破局是最好的,风雨几重,孤同她一起担下,比一味瞒着她好!”
薛灵枢闻这话,倒也点了点头,却还是忍不住道,“……那是否突然了些!”
“自然也不尽于此,她没殁……”贺兰泽缓缓止了声息。
回想这七年里的种种摧心剖肝,无非是那一次她的言而无信。很多时候他想若是她当时直接说不跟他走,或许他会少恨她几分。
又想重逢后的种种,那场大雨,那间飞鸾坊,无非是为了一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