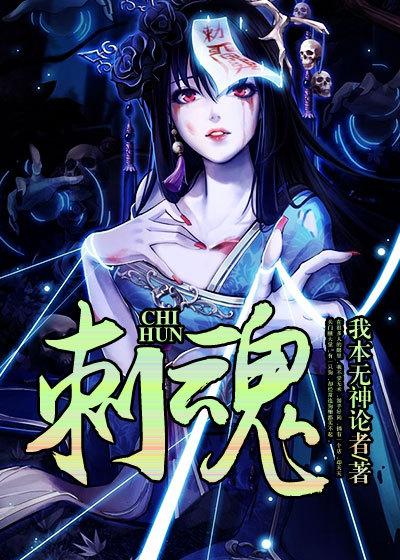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倩女传奇电影在线观看 > 第一百〇五章 同命相连(第2页)
第一百〇五章 同命相连(第2页)
缓了半刻,鬼母的脸也泛起酸楚,带有些许颓丧,道:“自由和真话该是一家的,崇尚自由,却不让人说真话。那你父母教导的自由,可见是虚伪自由。”
庒琂听之觉得入理,便脸红耳赤,道:“我发肤受之父母,父母冤死,他人在背后议论,贬说,难道不该为之生气么?”
鬼母笑道:“啧啧啧!说你这人好,果然是好。我眼睛虽然瞎了,瞧你的心地,我觉着庄府的地儿,不该容你。话说烛灯红红,碧酒绿绿,长久以往,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丫头,我没当你是个陌生人,才跟你说这些个话。算个缘分吧!你不爱听,那我便不说了。横竖我欠你一顿吃的,等出去,我寻你报答便是。”
庒琂怪道:“你说的也有理。”盯住鬼母的眼睛看,看了好一会儿,再说:“我这人也不图别人报答什么。我欠别人的都没还清楚呢,何苦增加别人的烦恼?”
她想鬼母这人落魄于此,先在地下见,又在这个密封的屋子见,想到的,只怕她也是天涯沦落,图她报答,怕是要增加她的负担。这才说此话语,以示安慰。
鬼母道:“你欠谁?欠了多少银子?你与我说,等贼丫头来了,我叫她拿来给你,你去还与他。这世道,欠不得人,也挂不得人的。唯独清清爽爽最欢心。”
庒琂摇头,道:“清爽,谈何容易。”
鬼母道:“你小小年纪,怎这样多悲欢离合伤感情触?我像你这样大年纪,已做大事情了。你说你十八,这年纪好啊,要是我的……”
说到这儿,鬼母忍不住哽咽,吞下后边的言语,不说了。
庒琂见她这样,再安慰道:“伤心的事儿,咱们不说了。说点开心的吧,反正,也出不去。我们为何不祈祷事事顺意呢。你说,是不是?”
庒琂本身就伤感不已,更不想看到他人也如此伤感,此处,安慰他人,也安慰自己了。
鬼母听毕,点头。
庒琂道:“才刚我问你,你说的贼丫头是谁?哦,对了,我怎么称呼你?”
鬼母呵呵地笑,道:“贼丫头就是贼丫头,你倒提醒我了,这许久也没留心她叫什么。等见了她,我问问,届时再回你便是。要问我名字,跟贼丫头说的那样,你瞧我这头发可是白的?”
庒琂捂嘴笑,点头道:“是呢,才刚吓死我了。一身的白。昨夜我以为……”以为见到鬼了,又觉得话语对人不敬,赶紧说:“以为是白衣飘飘,踏着祥云的观世音菩萨呢!”
鬼母乐道:“都是女子,你的说话叫人听了舒服,那贼丫头得跟你学一学才得。既然你也说一身白,就是白了,白发鬼母便是。”
庒琂愣道:“鬼母?”
遽然觉得,有人看得明白,有人内心明白。看得见的未必明白透彻,看不见的反而黑白分明。这位鬼母如此自称,可见她在自嘲,自己明白着呢。这样的人,想必身世也如自己这般曲折凄婉吧。
一来二去,两人惺惺相惜,相互倒觉得是已久未见的故人。
言语间虽有些许陌生,心里却已近在眼前。
鬼母的说话戾气减少几分,庒琂逗人斗嘴的言语也少几分,真情倒是吐露不少。
至此,庒琂对鬼母身份,以及她的失明有些疑惑了,因问:“有些话,不知该不该问?”
鬼母道:“你这丫头心思多,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你父母不是教你自由为贵么?这会子,怎畏手畏脚,吞言吐语的?”
庒琂嘻嘻一笑,道:“是了,是了!”重整话语条理,道:“那我问你,你不许生气。可好?”
鬼母道:“依你了!这处地方难得有个人陪伴,再生气也不会赶你走。你说吧!”
庒琂心满意足,终于寻得一个迁就自己的人了,又仿佛错觉此人说话,行为有些许像母亲,故而往下说话有些肆意,她道:“你的眼睛为何这般?”
鬼母笑道:“这话能问,居然怕成这样,难为你的心了。那我告诉你实话,我这眼睛是哭瞎的。”
庒琂震惊,悲悯,直直盯住她,久久不敢言语。
鬼母怪道:“怎么?吓到你了?我的眼睛瞎了,是不是很可怕?”
庒琂连连摆手,道:“不不不,不可怕。”
鬼母又道:“那你觉得可怜?”
庒琂顿住。
鬼母显得有些生气,道:“哼!可怜人之人,必比可怜人更可怜,更可恨!我不需要你可怜我。我有的是金山银山,就算我瞎了,我也有天下,有享受不尽的荣华。你要是识趣,对我好一点儿,说不定,我真全部传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