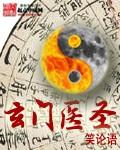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卫家女最新章节 > 携势你真以为天意永在你侧 (第2页)
携势你真以为天意永在你侧 (第2页)
赵启恩显然是气急,为了卫行歌,他对定远公也不复昨日的和颜悦色。
卫蔷站在他面前,低头不言。
恰此时,卫行歌已经在偏殿换了衣服,头还湿着就僵着两条腿大步走入了文思殿。
“圣人,此事与国公大人无关,是微臣行差踏错,国公大人罚我,是为了消磨我胸中戾气,不然,微臣怕是会犯下手刃朝中大臣之大罪。”
说着,卫行歌就想跪下,还是被两个小黄门给死命扶住了。
“手刃大臣?你想杀人?究竟是出了何事?”
卫行歌避开两个黄门扶着的手,勉强站定,低头道:“圣人,微臣察觉有人想要干涉禁军防务,可微臣并无实证,昨日微臣被灌了酒,胸中杀气横生,几度想要直接去手刃了微臣怀疑之人,再自戕谢罪,保禁军无恙。是微臣想错了,圣人是仁厚之君,为了微臣,明明身有不适还夜召国公,是微臣莽撞,微臣惭愧,圣人之恩如山如海,微臣肝脑涂地亦不能报!”
方才赵启恩疾言厉色,卫蔷脸上也只是挂着恭敬的表情,听着卫行歌行云流水一般的言辞,她微微转头看了一眼。
“你先告诉朕,是谁要动禁军?”
“回圣人,是兵部左侍郎何郸,连同他手下兵部众人一直结交禁军中人,从前,微臣以为不过是寻常交游,没想到昨日微臣还未进城门,就被何郸下属兵部库部主事李势拦住,邀我去喝酒,他们与昭武副尉刘充奚勾结,席上连番问我国公掌兵之时粮草、军饷调度等事。
“微臣虽不喜饮酒,最烈的玉烧清也是能喝两壶的,昨日不过寻常米酒,却突觉头脑昏沉,微臣察觉不对,拔刀欲起,恰好下属闯进去告诉臣国公归朝,臣酒意上头,本想杀人之前先叩谢国公大人,却被大人察觉异样,命臣醒酒……惊扰圣驾,臣实在惶恐!”
这一夜,东都城内还是不太平,紫微城中一道旨意,禁军羽林卫便如饿狼一般扑入了兵部多人家中,果然在兵部左侍郎何郸的书房里现了交代属下笼络禁军怀化郎将的书信,甚至在昭武副尉家中找到了致人晕迷的药物,更现其党羽竟然私下做了一本禁军将领名册,里面记录了许多不堪之事,显然是为挟人为自己所用。
最离奇的是兵部库部主事李势在禁军闯入之后以短刀杀死两人服毒自尽,在其床下现了□□兵器,经辨认,是南吴所制。
明堂震动。
“天天与我说朝中无事,这就是朝中无事!是不是等南吴悬刀于朕的榻前,你们还会告诉我朝中无事?!”
赵启恩继位七年以来,行事和缓,待臣下柔善,罕有如此震怒。
满朝文武一时不敢吭声。
“姜尚书,何郸乃是你的门生,你能否告诉朕,他怎么就能把手伸那么长,还让南吴的探子给钻了空子?!”
姜清玄脱冠请罪,最终被罚俸一年。
既然有罚,也要有赏,赵启恩想给卫行歌提一级为游骑将军,却被一人拦下了。
那人就是卫蔷。
她穿着一身黑袍,站在武将之,原本是面无表情,仿佛诸事与她无关,到此时她却站了出来:
“启禀圣人,卫行歌本无将此事告知圣人之意,乃是圣人心怀仁德,关切臣属,方有此次灭敌于先觉,再说卫行歌毫无防备,竟与南吴探子同席饮酒,就算真有些许功绩,也是功过相抵。”
赵启恩看向她,终于露出了今日第一次的笑。
“罢了,朕听国公的。”
此时,不过是镇国定远公归朝的第三天,在皇后被削权之后,姜家凭借门生故旧在兵部中延伸的势力折损大半。
从明堂出来走出紫微城要走过长长的御道,姜清玄缓步徐行,从前,他身后总是簇拥着无数的门生,颇有一人掌半朝之势,今日,他走在前面,无人敢与他攀谈,一众寒门出身的朝臣走在他身后,犹如一群被掐断了脖子的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