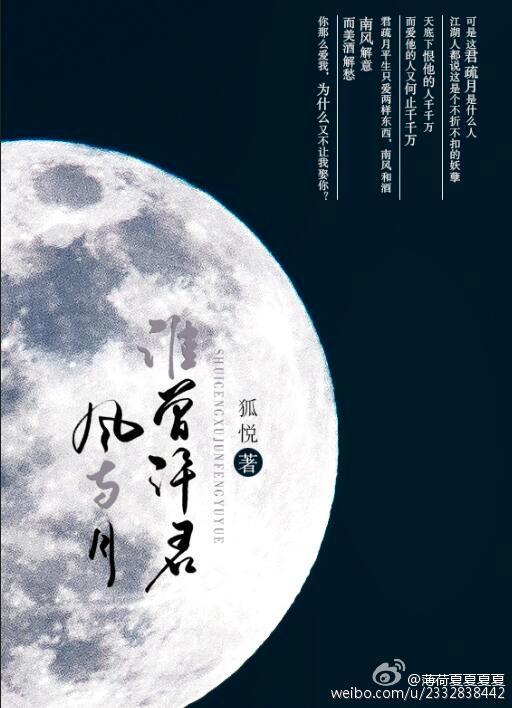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破烂事儿男主是有几个 > 第046章(第1页)
第046章(第1页)
段乔个想的简单的,受惊的眼睛染上点怜悯——
说实在的,她心里没半点主意,更是一点主心骨都没有,巴不得所有的事,有人都能指着她往前走,别叫她用脑袋来想,想太多就容易出事体,对,她一想说出事体,原本还恨恨地瞪着人……
这下子就一点都没有了,难不成他就想试试他行不行,才找的傅悦?
而他们都搞错了,以为他只能傅悦一、一起才、才能那个?
还有这种事?
她傻啦吧叽地盯着他,好半天没出来声。
“想什么呢?”
他仿佛没看见她脸上的震惊,伸手将她掉落下来的发丝给轻轻地拨到她的耳后,小巧的耳朵,微微红,透着个羞怯的娇样,他一碰,似乎觉得那颜色又红了那么一点点,不由得以指尖刮过——
轻轻地一刮,一点力道都没用,就能轻易地察觉到她的颤抖,从他的手指底下传来,眉眼笑得更开,迎上她的怜悯,仿佛一点都不在意,“我们得好好生活,你说是不是?段乔?”
问的真好,问的她的心都快跳出来,——手堪堪地就捂住她自个儿的胸口,眼皮子没敢抬,甚至都没敢去看他的手,就是那么轻轻地一刮过,她都觉得耳垂像是烧了起来,那火火烫火烫的,似乎她的人都能跟着烧起来——
这种想法,叫她打了个颤,破天荒地抬起眼睛,与他对视,那双黑色的眼睛里,只看到他黑色的瞳孔,脸上笑着,那笑意分明浮于表面,一点未到眼底,让人看着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避开他的视线。
他的视线仿佛是个毒汁,看一眼,就能把人毒倒了,而她就种感觉,而话更是像一种威胁,一种宣告,嘴巴比脑袋反应的更快,“好呀,有什么不好的,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想要好好过日子了?”
她顿时就有个了主意,都说自私鬼都是为自己想的,她就这样子,隐忍着,再给人重重的一击,难得有主意的脑袋——真个是难得的,她还有自己的主意,还晓得干什么叫隐忍,晓得给高炽难看!
对,她的想法就简单,他不是看到那什么的才能行嘛,那么一辈子都叫他看不到,看他还能不能硬得起!
想法直白的叫人喷笑,偏她想的是一本正经,对自己的主意一点怀疑都没有,难得的信心十足,人藏在水里,巴不得这水老深,深的叫她深深地藏在里头,“高、高炽?”
也就一开始叫他的名字会结巴,都两三年了,再结巴的毛病都改了,现在突然的就那么的结巴了,完全倒退了——
“又结巴了?”高炽颇有兴味地看着她,手指还从她的耳垂落下来,落在她的喉咙间,人就半蹲在浴缸外头,却是比她还高,高出她大半个头,还凑近她的脸,呼出的气儿就吹着她脆弱的眼睫毛,“你是怕我了?是我吓着你了?”
一连问的,问得她赶紧的低下头,眼睛就光着水,透明的水毫不客气地暴露她的所有,即使是盘腿坐在水里,也没能让她感觉好受些,以前没有什么,现在她觉得如芒针在刺,走着走着,前面一大段路都是平坦的,没有危险的——而就那么的猛然一下子,地上就出现了个坑,她一步子往前,人就掉了下来,再也爬不上来!
她摇头,心里心虚,又不敢当着他的面坚决否认,否认也是要勇气的,她可不就是没有这种东西在身上的嘛,什么气节,什么不为五斗米而弯腰这种事,都离她太遥远,远的都几乎是太阳与地球的距离。
“我怕、我怕什么呀,我要、你怕你吗?”
还真有硬气一会儿,她居然还梗着脖子,声音还挺重。
他一笑,笑得极好看,像是把天底下所有的优点都聚集到他的身上,“我怎么听得这么假呢?”他还朝她吹气,几乎是跟小孩子般得意地看着她下意识地闭上眼睛,那神情更得意,“段乔,我不管你,随便你怎么着,我都行——”
随便怎么着都行?
这种话听上去怎么就这么奇怪的?
就段乔这样的人,也觉得不对,她一直心虚,面对高炽心虚,觉得自己对不起人,可现在——完全是跟个奇葩事,她能听不出来这话的意味才是怪事,他家不拦着她向外发展,妥妥的一个“新时代”丈夫?
还是她到了女尊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女人为主了?
“你蛇精病!”她真骂人了,还是头一次骂高炽!
人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哪里管身上全是水,怎么都吞不下这种荒谬的感觉,包着浴巾就去找她自己的换洗衣物,扒拉着往身上穿,不管不顾地拿着包就要走人,再也不想见到这个男人——
“蛇精病?”高炽疑惑地看她,见她弯下腰,浑圆挺翘的臀部刚好对着他的方向,嫩白的肌肤都夹杂着一点点痕迹,尤其是在嫩白的肌肤上,那些非常的明显,看她去套裤子,把个小裤裤往上拉,一下子就把他的视线给挡住了,他两三步就走出卫浴间,伸手从后边过去,就去摸她的小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