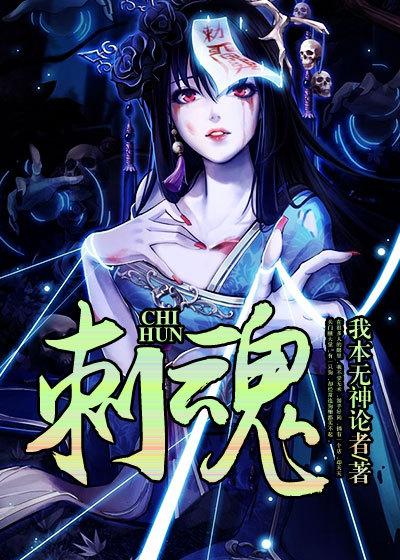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宿醉之后第二天怎样能更舒服 > 第726章 15 穷途末路(第1页)
第726章 15 穷途末路(第1页)
()”
阿月坐在主审台后,冷眼旁观着底下众人,她的眼神一一梭巡而过,待她看到底下角落中站着的流锦、摄魂、结魄、幻术等人,她慢慢朝着他们勾了勾唇。如果他们今日敢有任何动作,等待着他们的必然是相同的下场。只是今日本该还有一人,她一直都在等着那人的出现,她为何没来?这场好戏若是缺了配角岂不有些可惜?她挽唇勾起抹讥讽的笑来,笑意未达唇角。
司夜离同样在看着她,她这身打扮很符合她的气质,将她衬托得很美。他想起那日她在地牢中与宁浩的对话,她此时的心情又是如何?他猜不透她的心思,现在的她越来越难猜,他几乎看不透她在想些什么。她可以笑着谈论风轻云淡的事,却又能在下一秒用几乎残忍的声音说出绝情的话。她也可以杀人不眨眼,哪怕那个人是她最亲近之人,她也能像对待陌生人般毫不在意,她是望月,她不是他所熟悉的小白。她已经又变成了那个用冷漠将自己伪装起来的望月公子,她的情绪藏的太深,以至于变得异常陌生。
侍卫押着司夜离跪了下去,眼前的他只是个阶下囚,他们对他粗鲁而暴力。阿月是眼看着他再次对自己下跪的,不同于以往那次,这次是他们身份使然,缺少了点旖旎色彩。她放在案台上的指尖微微颤抖了下,被她很好的掩饰了。她缓缓撇开眼不去看他,眼眶却不小心瞥到身侧芷澜捏紧的双手正搅在一起。阿月目光向上,并未看到芷澜有什么异常。许是发现到她的注视,芷澜低下身来问她有什么事。
许是她敏感了,就算芷澜紧张或害怕将手搅在一起也没什么,她到底在怀疑什么。阿月抬手拍了下惊堂木,示意肃静道:“堂下犯人罪证确凿,判为剐刑。”她轻描淡写的将剐刑说完,像是在说件无关轻重的事。底下众人皆都哗然,剐刑换言之就是千刀万剐,要将人的肉用最锋利的刀一片片割下,直到剐满千刀流血而尽。这种死法太过残忍,若是对任何一人他们不会有这种想法,可那人毕竟是百姓爱戴的司相,他的皮囊又生得这般俊美,真要是这个死法,想必也会让人受不了。这可是最残酷的刑罚,没有之一。
底下议论纷纷,抗议声随着阿月的话四起,几个情绪激动者甚至想要冲上前来找她理论,嘴上说的话自然就不客气道:“你好歹也是司相明媒正娶的夫人,做人怎么能这么恶毒,不要以为你现在当上了公主就能耀武扬威,想怎样就怎样……”
“你这个恶毒的蛇蝎女人,相国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你会得到报应的,你的下场会比他还惨……”口诛笔伐者继续在疯狂谩骂着。
众人都以为阿月不会回应,她之前对所有的谩骂都只采取了一个态度,就是无视。要知道那些人根本伤不到她,无非就是想借此出口恶气,还有些人云亦云之人哪里知道什么是非对错,不过是听人教唆罢了。就像先前阿月被册封为公主时一样,都是在褒贬声不一中进行的,同情她的人有之,但对她辱骂之人更是有之。她反正现在是毁誉参半,早就无所谓了。她本就不是世俗所认同的那些人。
阿月站起身,缓慢朝着司夜离的方向走去。话是对着先前那些人说的,“瞎了眼么?”她撩唇轻启道:“的确是瞎了眼呢。”像是在自问自答般,丝毫不在意冷场。底下众人早就被她的话给震惊了,心道连她自己都这么说,真是可怜了司相会娶这样的女人。
晌午的日光越发浓烈,炙热的阳光照在头顶有种烈日灼烧的感觉。她一步步朝司夜离走去,满头的珠翠琳琅翠响,迎风发出细微的叮当声。她居高临下看着司夜离,抬手轻挑起他的下颌,由她做来有种轻佻的感觉。司夜离的眼中洒落了细碎的金光,晶亮的眸底倒映着她的身影。她以为她所看到的又会是一片暗沉,但他清楚告诉她,这一次什么都没有,没有阴谋诡计,没有利用,有的只是对她的一颗真心。她被惊到,蛰痛般放开了他。
她在害怕什么,害怕会被他的眼神蛊惑到吗?阿月从衣袖中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张绢帛递给他道:“这是和离书,自此后你我再无瓜葛。”她的话语冷淡,似冬日寒冰不可融化。身为公主,她有资格提出同他和离,但她的做法却是无法被理解的。她在司相落魄时离他而去不说,还要当着世人的面羞辱他,这样的女人是难以被世俗所容忍的。众人又要对她谩骂,司夜离抬起手止住众人的说话声。场上静得仿似只剩下了他们俩的声音。
阿月转身要走,就听得背后司夜离声音低沉清浅道:“小白,那日婚礼上我其实是安排了李若素、若兮、若骞三姐妹向你叙旧的,不知你是否忘了,当年他们被人欺负就是你救了他们,后来你想推行女革,我就想到他们,与其让别人来帮助,不如靠他们自己变得强大,既然他们有想法,将来必有出息的一天。现在他们自己开了个小私塾,专门给女子教书,你看这不就是在一点点进步吗?”可惜他的良苦用心她都看不到也不想看不是么。
他轻轻笑道:“小白,如果我死了你可否能原谅我,不是嘴上说的,而是心里真的对过去放下了。”他似乎叹了口气,声音很低沉,沉到就像是突然而来的乌云遮蔽了毒辣的日光。他说:“玄月宫已不再是你的责任,你没有必要将那些扛在自己身上。你已没有恨的必要,他们不值得。可若是我对你犯下的错,能不能在我死后就让那些都过去呢?”他的声音中似有恳求,那么低声下气只为对她。
阿月的脚步停滞,她想要往前,双腿却不听使唤。她面色冷漠,淡然道:“好。”这声好既是对他的承诺,也是对自己而说。宁浩已死,玄月宫已是过去,连她也要走向另一条陌生的路,还有什么好放不下的呢。或许还是有的,比如说那些隐秘不能言说的事,始终都像是根无法拔除的刺,扎在她心上,不得解脱。但既然答应了,她也想让自己做到。这是他们答应彼此最后的事了,自此后他们再无瓜葛,当真就毫无关系了。
司夜离指尖颤抖着将和离书塞到衣袖中,唇瓣惨烈地划出一抹笑来,到最后她还是要离开他不是么,他做了这么多依旧无法挽回她的心,究竟要如何他们才能重新开始?
小白,但愿我这么做是值得的,就算不值得,我也不后悔。
“行刑。”
阿月最后落下这两个字,广场正中央邢台上站立的两人朝司夜离走去,他们手中一人持一把硕大的刀,刀锋被磨得异常锋利。他们将司夜离绑在木桩上,脱去了他的上衣,行刑的壮汉一人提一碗酒,自口中饮入后喷在刀身上,冰刃的刀锋散发着森森寒光。
流锦实在看不下去,几度欲要冲上去,但他们几人的正前方被不少禁军围着,一旦他们动手便会被冠上谋逆罪论处,皆格杀勿论。这是司夜离最不愿看到的,他们的武功他不担心,但他不想因为他而将事情搞得越发复杂,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总要有个解决的法子,外人是无法干涉的。他们也只是白担心,什么忙都帮不上。
摄魂拉住他摇了摇头道:“主子的命令不得违抗,若你实在不忍就别看了。”他们又何尝难忍心疼,然而他们知道唯有这样才是始终,那必定也是主子想要的结果,哪怕是死。
行刑开始,壮汉提着的刀就往司夜离手臂上砍去。锋锐的刀锋带出一串血珠,此人割得又薄又好看。底下众人却都是倒抽了口凉气,有胆小者甚至当场晕厥过去。那些支持司夜离的人企图想要上来劫囚,被御林军武力镇压着无法动弹,一度场面失控。他们怎能看到这位倾国倾城的相国最后会落得这个下场,既然无法冲上去,他们就转换策略,改而去攻击阿月,企图挟持她来威胁交换。终究是徒劳,那些人根本连主刑台都爬不过去就被人拦住,将闹事者当场处决,以来控制场面。还是有用的,毕竟那些人死后吵闹声就小了不少。
阿月被吵得有些头疼,她抬手微微撑着自己的太阳穴,看着刑罚继续。司夜离在忍着痛,一刀两刀,当第三刀由另一人落下时他的额头上明显因忍痛而流下汗来。他面朝着阿月,所以她最是能将他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她像是在无动于衷地看着场表演,无论台上的演员是如何精彩似乎都激不起她的情绪来。
芷澜不知是被这种剐刑太过残忍所刺激到还是内心实在惧怕,她伏低下身在阿月耳边哀求道:“小姐,你能别这么对相爷吗,奴婢求求您了,相爷这些年真的很不易。您就算真想杀他大可一刀砍下,为何非要这般折磨呢?小姐不觉得这么做实在太残忍了吗?”芷澜在阿月的目光中怯懦说完,指责的声音越来越小,但她紧握着拳,大有种阿月若是不松口她就自己冲出去的架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