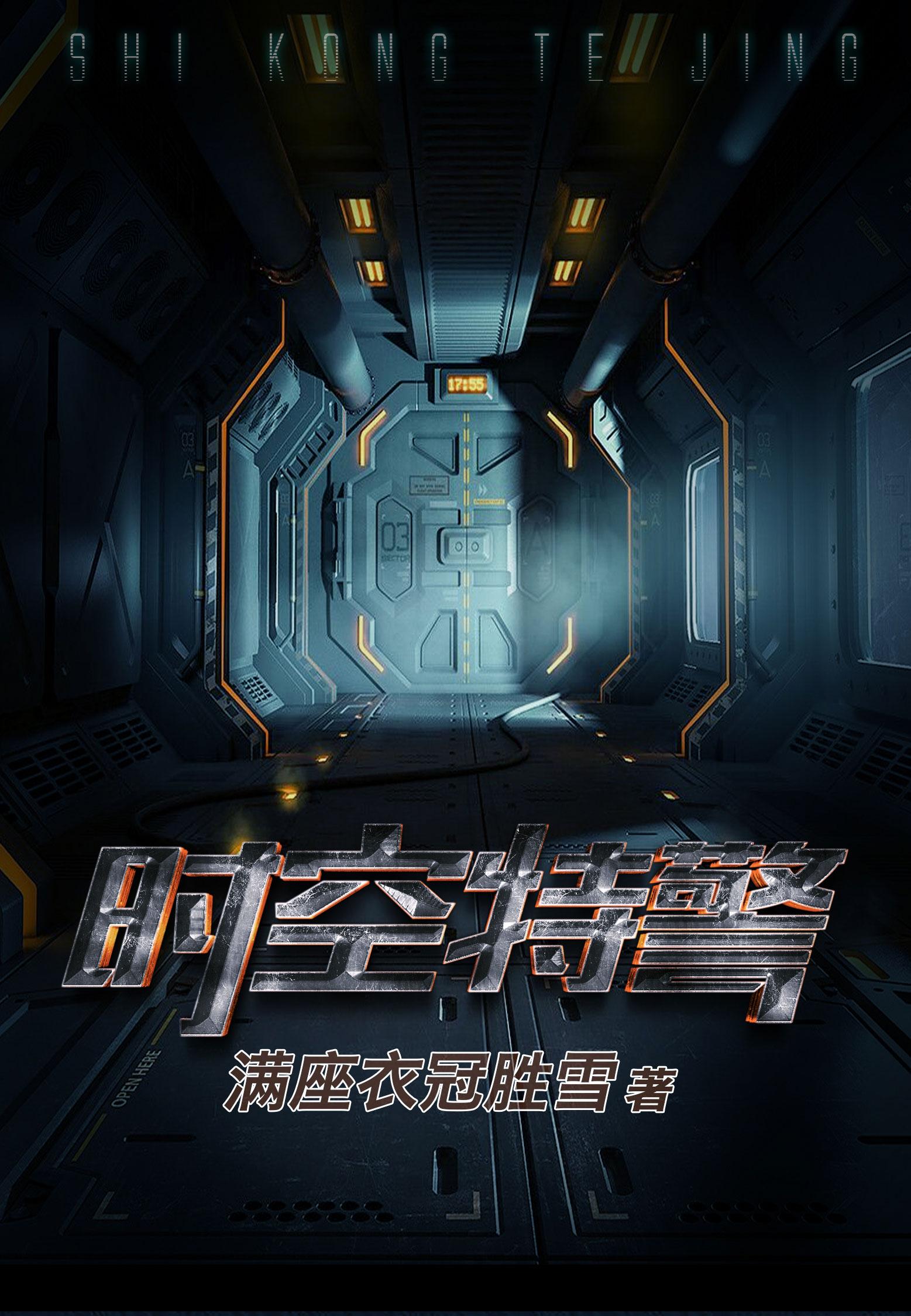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掌心痣图片大全 > 第160章(第1页)
第160章(第1页)
陆晚只怕是冻得连知觉都无,以至于流血了仍不自知。
车上有简易拖鞋,他找出来给人换上,大掌温热,动作轻柔,好似捏的是件易碎的古董瓷器。以陆晚的角度,看不到祁陆阳的脸,也不知道他的表情,她眼前只有男人如山般宽广的脊背,和漂亮饱满的后脑勺,以及,执着她脚腕的,修长有力的一双手。
这双手曾经拂过陆晚的发顶,耳际,脸颊,胸前,以及其他所有地方;她和他曾经拥有过无数亲密的时刻,比现在这种接触要亲密许多,可是,陆晚现在却觉得,没有哪一次亲密,带来的震动如此之大。
男人指腹所到之处,都在燃烧,燎原之势,不可阻挡。
换做以前,每次被祁陆阳抓住脚腕的时候,陆晚都会下意识地躲开挣扎,今天却乖得不像话。她祈求这个人能多触碰自己一会儿,她想抓住祁陆阳的手,贴在脸上,或是捧着人吻一吻,甚至做更投入、更过分的事。
‐‐陆晚真的有这种冲动。
什么道德,什么界限,什么应该不应该,陆晚都不想管了。
可最终,她也只是流下了一滴泪。
泪滴在祁陆阳的手背上,他惊得直起身来,正对上陆晚凄然的眼。她看起来忍了很久了,也不想再忍,她张嘴想说什么,祁陆阳赶紧用手指按在人唇上,指了指她身边搁着的手机,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随后缓缓摇头。
他的意思再明确不过:陆晚的手机,被人监听了。
原来,祁陆阳比陆晚,更了解庄恪。
无需多想,陆晚就认定祁陆阳的推测是对的。她惊惧不已,无法说出半个字,祁陆阳拍拍女人的手以示安慰。他用唇语说:
迟迟,你过得不好。
虽然听不到语气,但陆晚知道,祁陆阳说的是肯定句。
陆晚拼命地摇着头,死不承认,只剩眼泪越流越凶。她抬手去擦,没有用,反倒搞得一双手湿漉漉的,脸上妆也花了,像个顾前就顾不了后的狼狈乞丐,衣不蔽体,偏偏还妄想守住最后一点可怜的自尊心。
祁陆阳抽出纸巾,细细帮陆晚攒着泪。手扣住下巴,他半是习惯半是放纵地把她的脸往自己唇边带,两人几乎呼吸相闻。
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因为阿全适时地打断他们俩:&ldo;庄太太,您是往家里去吗?前面就要转弯了。&rdo;
看似老实巴交、不善言辞的司机,只用一个称呼就点醒了在危险边缘的两个人。
不过几厘米的距离,瞬间变成几亿光年,祁陆阳率先坐直了身子,他笑笑,语气中一丝破绽也没有:&ldo;你看看我,只顾着看你伤得严不严重了,都没想起来要问。是直接回庄家去吗?&rdo;
陆晚说是。
祁陆阳让阿全停车,嘱咐他:&ldo;天气不好,看样子也许要下雨。你直接把人送进院子、到楼下去,务必看她进屋再折返。&rdo;说罢,他看向陆晚,&ldo;我这边不方便,就不跟着了。&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