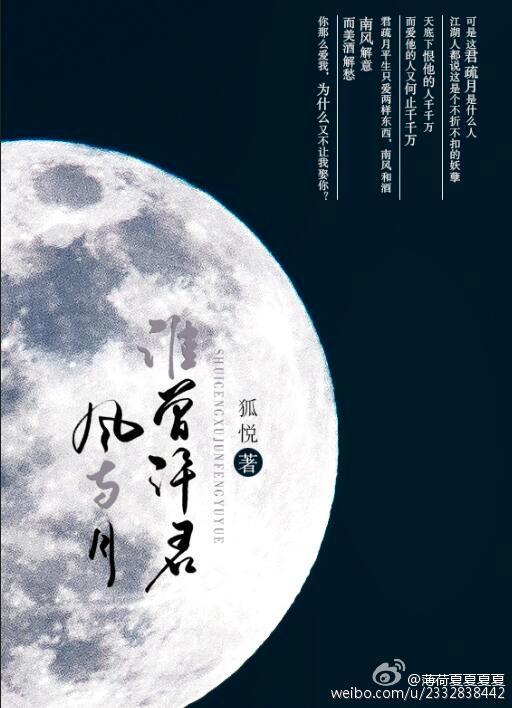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重生成为偏执的心上人 > 第9章 昔日恩情(第1页)
第9章 昔日恩情(第1页)
苏姌眨巴了下眼睛,谢浔迅速挪开目光,默了片刻,“微臣只是不想要一个三心二意的盟友!”
苏姌“哦”了一声,藕臂再次攀上谢浔的脖颈,歪着头娇笑,“好啦,听你的就是了!有大人在,外面那些野蜂浪蝶哪会入得了本宫的眼?”
明明是亲昵的哄慰,笑意却不达眼底。谢浔知道这并非她的真心话,可堵在心头那团郁气还是疏解了不少。“还望公主信守承诺!”
他一手掐住苏姌的细腰,另一只手将一支发簪戴在苏姌发间。苏姌伸手去摸,谢浔拦住了她,“不过信物而已,时时提点公主注意言行!”
谢浔话锋一转,“公主打算怎么做?”
苏姌也不再关注那簪子,肃容道:“江远一死,江家必定不会善罢甘休,我和大人一起把江家的水搅浑,越浑越好!”
谢浔抬眼,瞬间了悟了苏姌的意思。掌握金矿几乎等同于富可敌国。稍稍运作,钱、权利自然滚滚而来。他们知道这个道理,皇帝和江家自然也知道。因此,金矿权绝不会轻易易主,除非……江家大厦倾覆。而江远好歹是江家嫡长子,莫名其妙死在疯人群,镇国公一定会跳脚闹事。做多错多,届时就可接机扳倒这颗盘踞南齐多年的老树。而想快速扳倒江家,合作,无疑是上上之策。谢浔与苏姌交涉完后,去客房烘干了衣服。正要往公主府外走,隐隐闻到苦涩的药味。公主府的人,来来回回,络绎不绝。青月端着盆子,莽头撞进了谢浔怀里。谢浔退后几步,但血水仍泼了个满怀。“大人,恕罪!”
青月忙俯身跪拜,“奴婢带大人去换件衣服,府中备有男子衣物。”
谢浔眉心一蹙。长公主府上竟然备着男人的衣服?很显然是给小倌穿的。谢浔自是不愿意,压了下手,“何事如此慌张?”
“回大人,公主心悸呕血的毛病又犯了!”
谢浔本随口一问,却不想竟知道了苏姌的隐疾。原来,这些血水是苏姌吐的?谢浔依稀记得在浴池中拉扯时,苏姌心口有一道狰狞的伤疤。那时,苏姌的面色就不对劲。谢浔碾了下手上的血渍,问道:“长公主何时患上了心疾?”
青月迟疑了片刻,支支吾吾道:“长公主幼时曾在一村庄迷路,后来遇到了……”“青月姑娘!长公主叫你呢!”
此时,一个嬷嬷打断了两人谈话,青月登时变了脸色,“可是公主又呕血了?”
“是啊,太医都讲了公主不可动气,你们是如何照料公主的?”
两人相携着去了。“幼时?心疾?”
谢浔望着两人背影,脑海中依稀闪现出尘封的画面。那一年,他才刚满七岁,被人丢在乱葬岗。大雨瓢泼,漫山遍野的野兽撕咬着尸体,发出恶臭的味道。可他五天没吃饭,太饿了,根本没力气跑。此时,尸堆里,探出一颗小脑袋。他想也不想,饿狼一般扑咬红衣少女,想喝她的血。那少女似乎也伤得不轻,两人扭打做一团,滚下山坡。可他羸弱,最终被少女摁趴在了地上,动弹不得。“这么弱还学人偷袭?”
少女冷哼了一声,刚要离开,却被一只手抓住的鞋子。他试探着一点点挪动手指,抓住她的脚腕。小心翼翼,却又不肯放手。他想活着。少女这才看清他身上满是伤,有些地方染了尸斑,都溃烂了。“你怎么还赖上我了?”
少女蹲下身,轻嗤一声。后来,他昏迷过去了,有温热的液体入喉。他依稀记得少女拿走了他腕上的佛珠,还在他耳边叽叽喳喳,“心头血都给你喝了,以后可不许忘恩负义,要还我的!”
……谢浔摆了摆头,转过身,公主府的门已经关上了。最后,落入视线的,是苏姌挂在院中的红裙。怎么和记忆里那般相像?救他的人不是江玉柔么?那串佛珠信物可是江玉柔还给他的啊!谢浔摩挲着腕上的佛珠,陷入沉思。*另一边,青月走近寝房时,苏姌正对镜梳妆。“走了?”
苏姌打量着青丝间那支红宝石发簪,形似梅花,熠熠生辉。美则美矣,可惜,美的东西往往有毒!苏姌随手扔在了梳妆台上。青月咬着唇,候在苏姌身后,“公主,奴婢泼了谢大人一身狗血。”
“想笑就笑。”
苏姌嗔了青月一眼。其实,青月是南齐十大高手之一,怎么会连盆血水都端不稳?若非苏姌授意,她也不会去触谢浔的霉头。但青月一想到玉树兰芝的谢大人,被泼得狗血淋头。还对着狗血,一派专注深情的模样,青月差点当场没憋住。“公主,谢大人还是挺关心您的。”
苏姌轻掀眼皮,眸光骤冷。青月吓得“噗通”一声跪在地上,“奴婢知错!”
“不长记性!”
苏姌睨了她一眼,“谢浔听到心悸之症,是何反应?”
“谢大人在门口出神了许久,看样子并不知道公主是他的救命恩人。”
青月有些不解,“长公主不是托江小姐告知谢大人此事了么?”
“果然不出本宫所料!”
苏姌讪笑一声。从前,苏姌就是对江玉柔太过信任了,什么少女心思都说与她听,甚至托江玉柔转交信物向谢浔表白。如今看来,江玉柔从中作梗,顶替了这份恩情。“公主被心悸之症折磨多年,好处却让江玉柔得了!”
青月愤愤然,欲夺门而出,“奴婢这就去告知谢大人真相!”
“站住。”
苏姌淡淡道。江玉柔知道这段过往的一切细节,手中又有佛珠信物为证。谢浔那般讨厌苏姌,又怎么会信她的空口白话呢?何况,重活一世,谢浔的心意根本不重要了。她只担心谢浔顾念着江玉柔,无法诚心与她合作,铲除江家。苏姌又将那支红梅发簪重新戴回了头上,正要出门。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公主,江恒回来了。”
苏姌推开窗,正见江恒站在门外,一双眼睛如毒蛇般盯着谢浔远去的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