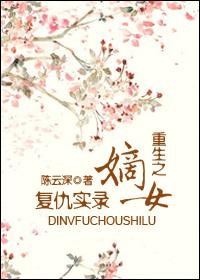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宠妃沾衣梅林 > 第二百八十四章 夜升烟火照阴霾(第1页)
第二百八十四章 夜升烟火照阴霾(第1页)
“不,一定是我想多了……事情一定不会这么糟糕……希望是我太多心了……没事的,应该没事,一定没事的……”宁暮试图说服自己,为这些无辜的船客们祈祷一线希望下来,但最后的几个字,却是越说越轻,越说越无力,无力地连她自己都有点不信。倘若,这一切都如同她所猜测的那样,事情会以最坏的方式发生,那到时,她又该如何是好?
难道,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无辜的人因为帝王的对外决定而付出生命吗?
可不舍得,又能有什么别的办法么?与天子做对,是大罪,届时天子迁怒姜家,如何收场?
是置身事外,还是一施援手?是为成大事不拘小节,还是人命关天不让生灵涂炭?
如果我是钟沉,又或者我是齐王虞庚……
宁暮双腿蓦地一软,竟慢慢靠住了船壁,兀自沉静了一会,握住了拳头,蹙起眉头,心想:我为何要作钟沉?要以他作为一个帝王的立场去想?我为何要作虞庚,以他的帝王的立场去想?却不能站在他们这些帝王的对立立场上去想?我为何要以帝王之间、为了霸业而寻找牺牲品的立场来思?我为何不能是别人,比如……爹?
倘若我是爹的话……以他的立场来思考,他站的是苍生,站的是百姓……
这个想法在宁暮的脑中急闪而过,犹如一道刺眼的强光,一下穿透阴霾湿冷的黑夜,隐隐为她带来了短暂的光明和温暖,她想起了父亲陆坤的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无论国家是兴,还是亡,最终受苦的永远是黎民百姓,一个帝王纵使有着统一霸业的野心,却没有同情天下弱者的心,那么,这个国家不久便会衰亡下去,宁儿,你虽是女子,但你却有着比男儿都优秀的才情,甚至,爹爹相信,等你长大后,你在军事之上的成就,依然不让须眉,你的善良,会打动一切阴霾,会替你开拓出一条光明之路,爹爹盼你,能够将这份执着一直保持下去,直到真的无能为力……”
宁暮回想起了在空雾山的日子,往事翩然浮起,父亲陆坤的话语在她的耳边响起,仿佛从来不曾消失郭,她身体的颤抖就那样,渐渐停止了,她握住自己的衣袖,然后一遍又一遍的回想着父亲的一些教诲——如果爹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不会见死不救,一定不会让这些无辜的人死的不明不白,因为他比谁都爱惜苍生,比谁都善良。
爹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救他们……然后就是像陆坤这样与人为善,对朝廷忠诚的人,最终却没能落得一个好下场,想到这里,宁暮又不觉暗自神伤,更加坚定了为父亲正名的想法,那些谣言都说父亲背叛了朝廷,他们说父亲是异国的奸细,他们凭什么这么污蔑一个正直了数十遍,不贪不腐的长辈,他们凭什么?
这次哪怕是错失除掉齐王的最佳机会,哪怕会因此阻断钟沉事先已补好的计划,她也要学父亲,宁可愧对天子,也不愧对天下苍生——那才是陆家人真正的处事之风。
是以,这也是她此刻最想做的事情:拯救船上的这些人,包括自己。
宁暮轻轻一掠头发,微微整了整自己的衣襟,示意两名南国暗卫即刻退离,并认真嘱咐二人:“事不到万不得已,莫要暴露了身份。我现在是宣国的梅妃,不是南国的怡岚公主,若有不时之需,以信号为准。”两名暗卫点点头,身影一闪,已自消失而去。这种接近是幻术的功夫,仅在半瞬之间,两名暗卫便没了身影,再看时,却见客房的门已经被风吹开。
宁暮暗叹了一口气,她心里已知下一步该怎么走,该如何做了。
夜幕渐落,月上天际。初春的季节,海上的清风月明,亦显得更加柔和。
宁暮走近主舱,吩咐船上管事的老王,忽然询问:“王师傅,这次出海,可曾带了烟火?”
王管事想了想,仿佛是经过宁暮提醒才想起,忙回过神道:“有,有有!帝京带来的浮水烟花堪称是天下之绝,出行之前,金老板还特意交代,让我等带了三箱,以备到天云镇后,献给那里的官老爷们,听说这几日将迎来水镇的泼水狂欢节,宁姑娘这一提醒,我倒是记起来了,瞧我这脑袋,这事怎么给忘了,幸亏你提醒了,不然到了水镇,我倒会把这大事给忘了。”
宁暮点点头,打断他,道:“可否现在取来。”
王管事呆了一呆,有些犹豫:“此刻取来?宁姑娘,你要这些烟火做什么?”
宁暮注视着海上的某个方向,淡淡一笑,说道:“当然是有用。王管事,这番良辰美景,船上来了像齐王这样的贵客,此刻不用,更等何时?”
王管事跟着侧目,见她所盯着的方向,乃是——齐王虞庚,皱了皱眉:“那行,我向金老板通报一下……”
宁暮点点头。
齐王虞庚此刻显然沐浴完毕,他换了一身蔚蓝色的新衣,正懒洋洋地倚在栏杆身上,披散着一头仍旧湿漉的乌发,手里晃晃悠悠地提着一壶酒,目光漫不经心地落在天上,仿佛正在赏月,却没在喝酒,他的这身衣衫,比之前所见的那身火艳的衣衫比起,明显沉郁了几分。
海风吹着他的乌发,看起来十分惬意。
宣国贵族崇尚礼学,严秉“君子当以自重而不威,”的教条,素里见惯了宣国皇宫里那些正襟危坐、铁面无私的正紧男子,今夜再看这个证歪身斜倚在桅杆身上的齐国君王,宁暮倒是觉得有几分新鲜,虽然素里这些风范在钟沉身上也曾看到过,但毕竟只是浅许的,然而这个齐王,却有着别人都不曾有的明媚潇洒之气。何时钟沉也能像他这么活着,恐怕他也不会那般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