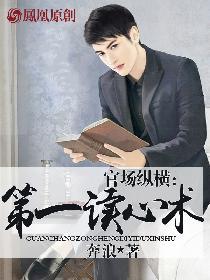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露水的夜 明开夜合讲什么故事 > chapter62冷与炽烈(第2页)
chapter62冷与炽烈(第2页)
车一路开往解文山的书店。
时间尚早,书店的玻璃门内还透着亮光,雕花窗棂镶嵌的玻璃窗户里,隐约可见解文山正坐在柜台后方伏案读书。
车在前方掉了个头,停在书店门口。
南笳抱着那纸袋下了车。
推门,门口铃铛一响,店里的人扶了扶老花镜,抬起头来,惊喜道“小笳?可有一阵没来了——快进来坐。”
南笳掌着门,笑说“等一下。”
她回头看了一眼,周濂月已下了车,落了锁。
待周濂月踏上路牙,南笳将门推得更开,周濂月走到她身后,抬臂撑住了玻璃门,南笳方才松手。
解文山更是惊讶,“……濂月,你也来了。”
他急忙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推开茶室的移门,几分局促地站在那儿。
南笳轻车熟驾地走了过去,推着解文山的肩膀往茶室里去,笑说“来找您讨茶喝来了。”
解文山去涮了烧水的小壶,接了净水,放在电磁炉上。
抬眼一看,周濂月已不坐他常坐的那单人的藤编椅,而是跟南笳一块儿坐在了对面的双人木沙发上。
两人膝盖轻轻挨着,虽无亲昵的动作,但自有一种难言的、排他的气氛。
解文山打开小柜子的门拿茶叶,打趣一句“喝什么?都喝碧螺春?”
南笳笑出声。
拿了茶叶,投入茶杯,解文山一边问道“你们怎么有空一块儿过来了?”
南笳听出来这句话的重音是在“一块儿”上,笑了笑,微妙的有点难为情。因为那时候是骗了解文山,才拿到了周濂月的电话号码。
周濂月倒是神情平静,“手头事情正好都处理完了,带她过来瞧瞧。”
话里意思一点即明,要解文山放心,“面子里子”的问题,早已妥善解决。
水烧到九十度左右,那控温的电磁炉自己断电了。
解文山提起水壶往杯中冲入热水,泡好茶,他在藤椅上坐下,瞧着南笳和周濂月,目光不无欣慰的意思。
这目光让南笳有点退却了,低头去瞅了瞅放在桌角的纸袋。
周濂月倒是坚决,拿了那纸袋,递给解文山,“一直准备给您,没找着机会。”
“这是……”解文山伸手去接。
“我妈的遗物。您跟她来往三年,写给她的信。”
解文山手一抖。
周濂月不动声色地瞧着解文山,“她叫我烧了,阴差阳错的没烧成。就物归原主吧,您拿着留个纪念。”
那纸袋似有千钧重,解文山托着它,手指颤抖。
片刻,他别过脸去,摘了老花镜。
“解老师……”
解文山咳嗽一声说“……小笳,恕我今天不继续招待了,你们先请自便吧。”
周濂月站起身,牵住了南笳的手,将她也从座位上拉起来。
周濂月往书店的储物间那儿看了一眼,又说“南笳存在您这儿的东西,今天我们顺便就拿走了。”
解文山抬手,轻挥了一下,叫他们随意。
统共三个纸箱,南笳抱了一个,周濂月抱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