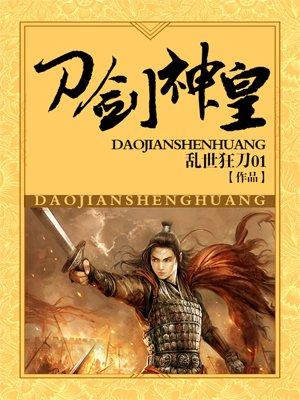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禁止入戏好看吗 > 第83章(第1页)
第83章(第1页)
不行!
我无计可施地捂住额角,阻隔自己不受控制的视线‐‐我真的很怕他。因为他的存在,永远只能让我看见自己是何等的肤浅和劣质。
他毫无所觉地拽了拽自己的衣领,嘴唇蠕动,但并未有任何醒转的迹象。我定了定心神,打定主意为他再解一颗纽扣就走。我低着头把手伸向他的衣领,没料想刚触着那颗冰凉的扣子,肩头却忽然被一双高温的大手扣住‐‐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我一时忘记了遮掩自己的脸,猛地抬起头来‐‐
我什么都没来得及看见,因为他沉重的躯体忽然像座巨塔般轰然倒下,我一时躲避不及,整个人都被他压在了身下。
据说声音通过固体比通过空气传播得更强更快,此刻我终于验证了这一点,因为我打雷般的心跳声正通过紧贴著自己的这具躯体传回到我自己耳中,振聋发聩。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似乎并没有醒来,在我因为距离过近而模糊了的视线里,他的双眼依然紧闭着。等我终于适应了那吓人的心跳声,并且重新找回思维后,我开始思考该如何脱身‐‐往左还是往右?
我单手揪住右侧的床单,企图借力使力,可我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被惊动了的他头部忽然向左一歪,整张脸就这么好死不死地压在了我脸上‐‐
我倒吸一口气,下一秒却没法喷出来,只能抽筋般地摒在了口腔里‐‐因为他的唇角,此刻正抵着我的唇角……
我脑中默念着本次日本之行的所有schedule,钜细靡遗的程度达到了连包车的车牌号都反复背诵了三遍。可这些完全阻止不了我此刻灼然欲焚的面皮,和全身皮肤尖锐到发痛的触感。我不敢呼吸,空气被割成无数细小分子,然后以史上最慢速度出入着我的口鼻。于是这又加强了我的症状,让我意识开始昏沉……
或许意志和意识从来都是相通的,否则,我的意志怎么可能变得如此薄弱?
我攥紧了身下的床单,微微转了转脖子,闭上眼,颤栗着贴上他的唇角‐‐那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触感犹如四肢百骸被齐齐过电,我终于被猛地电醒‐‐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能剧烈呼吸,动不了,身体又热又重!他却依然一无所觉地死死压着我,我试着转动自己的身体,以求和他之间撑出fèng隙,却不想他头部受到牵引而滑下来,双唇整个重重擦过我的嘴唇,然后一头垂落在了床上。
我失神地微张着嘴,那灼热而粗重的刹那像枚重拳般击懵了我,我在他身下愣了很久,才终于抱着破罐破摔的决心一把推开了他。他依然没醒,转了个身又不动了,看来着实醉得不轻。
我几乎是逃出他家的。
彼时的街道已被一层薄薄的积雪覆盖,那是在国内难以见到的大雪,真正如同鹅毛般宽大密集,打在脸上居然生生作痛,我顶着风奋力地向前走,直到双眼被染成一望无际的白。
那么冷,那么痛。
心里的热流在撞上这冰冷空气的刹那,忽然哆哆嗦嗦地死去了,尸体从眼眶深处涌出,在脸上结成冰霜。
街上已然空无一人,连个出租车的影子都没有。我拖着麻木而僵硬的双腿机械地走着,或许走了10来步,或许已经走了半个世纪。
我忽然蹲下,抱住自己的膝盖,把头埋进这个可以暂时挡住风雪的小小空间。在这个无人注视的异国街头,我允许自己短暂地败给这场突如其来的寒流。
假如我当初选择了保护他,那现在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泪是热的,心却是凉的。我用力捂住那些嘶哑的悲鸣,仿佛这样才能压制住那些不可能挽回、不应该挽回、甚至根本不该产生的后悔。
任熙悦,无论是冰天雪地还是艳阳高照,从今往后,你永远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待续……】
☆、【番外】‐‐名古屋の雪:秦空篇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喝了多少杯‐‐因为此刻我所能叙述出来的一切,都已经是建立在两天之后的意识了,所以我不太确定我所说的一切究竟哪些是真实发生过,哪些又是幻觉杜撰出的画面‐‐
总之那一天,为了一个不超过十个字的广告歌,我陪厂商喝了一整晚的酒,最后我按着烧灼的胃袋,昏昏沉沉地被扔在了离家300米处‐‐因为即使不清醒到这样的程度,我依然不愿被他们看见我那寒颤的住所,因而影响这笔来之不易的生意。
胃里翻江倒海,灼热的潮涌一阵紧过一阵,让我的胃几乎陷入痉挛。我听着自己重如喘息的呼吸声,努力想要稳住脚步,双腿却不受控制地歪扭着,仿佛一对积怨极深的爱侣,无论如何也不肯朝一个方向前进。
在意识到自己快要摔倒在地的当口,我只能快步冲到眼前唯一可以依附的一棵行道树上,暂时稳住自己,好半天才回过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