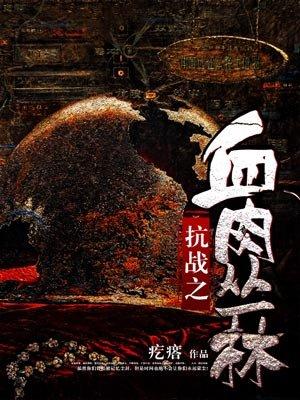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续倚天屠龙记完本 > 第73章(第1页)
第73章(第1页)
张无忌道:“现在连鹤笔翁也成了明教中人!真是可笑!这次丐帮在荷花峰聚会,最好玄冥二老的新主子陈友谅、神衣门的使君都能出现,我定要一一铲除!”
赵敏道:“神衣门的使君么,极有可能到场,但不见得会现身;而那个陈友谅么,我说他决不会到来,更不会现身!”
张无忌道:“对,丐帮上下恨陈友谅入骨,他若现身只怕事情要糟。”
赵敏道:“陈友谅一心图谋大事,这种事对他来说只是旁支,他不会浪费时间亲身犯险。但现在鹿杖客突然冒出来打伤了鹤笔翁,看来此事神衣门又棋先一着,今夜此处定有大的举动!快唤周颠穿衣提刀而睡,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开门出来,一切看我的举动行事!”
张无忌大惊,但见赵敏表情严肃,不似说笑,便依言下床走到与周颠睡觉房间的隔墙边,暗运内劲将墙敲了数下。这几声敲击,声音低沉却不扩散,直传到周颠睡觉的床上,周颠虽睡得甚沉,兀自如脑内擂鼓般一惊而醒。只听墙上传来张无忌的声音道:“周大哥,今夜可能有事,快穿上衣衫睡觉,万勿出来,一切看我们行事!”
周颠心中大喜,心道:“最怕无事!如此甚好!”便敲墙应了一声,穿衣着鞋抱刀而眠。
张无忌回到床上,赵敏已经穿好了衣服,张无忌摇了摇头,也跟着做了。两人和衣躺倒,张无忌问道:“敏妹你从哪里看出今夜定要出事?”
赵敏道:“鹿杖客的出现绝非偶然,他料理了鹤笔翁后一定就是南山妖丐!今天是腊月二十,距二十三仅两天而已。他们还有其他目标,今夜找到此处不做,更待何时?这神衣门的主子当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心狠手辣,处事干脆,有密谋、有计划、有目标,若在以往,我定要厚利结纳,否则坚决除却!容他多留一刻都生祸患!”
张无忌道:“也不知麻寻天会不会也成为他们暗害的目标?”
赵敏道:“非但麻寻天,假如是我,便是那史姑娘和掌棒龙头都走不了!但后两者却不能杀之,只能用之!”
张无忌握拳道:“对!掌握史姑娘,操控掌棒龙头!便如成昆操纵少林大会一般!”
赵敏点头道:“但其人心狠手辣不在成昆之下,又绝非因泄私愤而产生的邪念,是以其志向和胸中城府远非成昆可比,所以他还有什么阴谋,我却暂时无法猜到,只能见机行事了。嘿嘿,仅就此事比起来,那陈友谅的才能还在此人之下。陈友谅其人,阴险狡诈、居心叵测有余,但又未免心浮气躁,急于求成,行事疏而不密。看来以后的江山,陈友谅是万万没份的。”
一席话听得张无忌叹服无已,竟忍不住叹道:“假若我去争夺江山,有你辅佐,再有明教百万英豪,天下英雄虽多,又有何人能与我相争?”
听此言赵敏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没有接言。张无忌豪情万丈没片刻便又握住了赵敏的双手柔声道:“我只是说说而已,怎会让你反叛自己族类?你别在意。再说,我对做皇帝、争霸天下的事毫无兴趣!以前汉族人纷纷起事是有一个共同目标,但现在,却为了争夺地盘和各自私利而互相残杀,这样的混战,我见到就会插手干预,见不到就躲得远远的,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赵敏又是一声长叹,道:“无忌哥哥,我也时常想,是我耽误了你的大好前程……”
张无忌一把将她搂到怀里,用脸颊摩挲着她的头发,说道:“怎么会呢?敏妹,你千万别这么想!其实早在我刚刚做上明教教主之位时就下定决心找机会不干了,完全与你无干!”
赵敏道:“假如我不是什么蒙古郡主多好?咳……”她其实心里实在有一些话,但犹豫了良久,终于没对张无忌讲。那便是关于明教,关于周颠的。张无忌不做教主,别人岂会不认为是她之故?自古红颜祸水,男子汉丢江山,又有多少人不怪罪于女人?是以明教固然怪罪于她,周颠更加不会例外。周颠不做他自由自在地游行散人,巴巴地跟着张无忌干什么?不言而喻,光看他每次看自己的眼神都能看得出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偷取赵敏的性命!然后使张无忌重掌明教。
想当初在高邮废屋内,与东瀛杀手交战之时,那两名差点杀死赵敏的蒙面客,便是周颠故意放过去的。赵敏当时就察觉了。
但是她却不忍离间他们的感情,只有独自默默承受,暗暗提防。周颠极难是她的对手,她倒不惧,但是光明左右使、彭和尚他们,就不好对付了。如果哪天当真要死在他们的手里,也只有认命了,只要孩子能平平安安的生下来就好了。刚睡觉时张无忌给她讲周芷若的事时,她也是因为想到了此节才更加安慰的。因为自己死后,总得有个能干的好女人来照顾无忌哥哥。如果小昭能甩去教主之职,从波斯回来找张无忌,那她才是真的死也含笑了。
两人一席无话,张无忌模模糊糊要睡去,约四更多时,突然被一阵幽幽怨怨、凄婉哀伤的笛声所惊醒。碰了碰赵敏,那笛声又近了许多,赵敏凝神间,也听到了。
这时只听那边的仇海英一声厉喝:“快起来!”紧接着稀里哗啦一阵响,想必那些八袋弟子被仇海英一喝之下也已发现这阵越来越近的奇怪的笛声,开始一跃而起,纷纷穿衣着袜。他们刚睡着不久就这么折腾,哈欠连天之下心里都是烦恶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