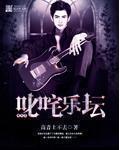《短篇脑洞合集》果实5
他带着我,我们一起在共产党的学校接受学习和教导。我们在指导员的见证下,在人民群众前举办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婚书是营长和指导员亲自写的并落得款。 50年,他跟着部队,一身单衣北上,我们骑辆自信车,骑了多少华里也没数儿,我就这么跟了一路,他见不得我哭,出发前只是和我说,若没回来,就让我找个好人改嫁。 后来呢,他回来了,带了一个二等功回来,一条胳膊留在了朝鲜。 我在文化部当秘书,后来虽然被政审,不停地写材料,但因为他也并没受太大影响。 别人要他这个战斗英雄跟我划清界限,他也不肯。 再后来,就前几年,他去了大会堂,也上了游行花车跟城楼敬礼。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秋实,秋天的果实,听上去就很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