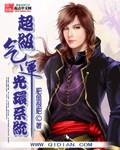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太宗为什么改成成祖 > 第63章 安西故人与故土中(第1页)
第63章 安西故人与故土中(第1页)
当李业带着效节军,抵达敦煌时,杨师厚在张淮深的协助下,已经基本控制了整个沙州。
这也难怪,短短一个多月的内战,和突然转变的局势,将归义军原有的利益团体和各路武装,都打乱了。
敦煌主要的几个汉家豪族,都卷入其中,如高家,站到了张淮深这边,而李氏、宋氏,都不同程度,卷入了索勋的叛乱。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既然有入局的决心,就理应有失败之后,被清算的心理准备。
当凉军驰援而来,迅速击溃了城外,由高昌回鹘和索勋联合的叛军以后,涉及整个敦煌的政治清洗自然不可避免。
跟随李业,闯荡了这么些年,杨师厚被锻炼出来的,不仅仅是军事能力,也懂得这些政治上权力博弈的规则。
所以,在击溃索勋以后,杨师厚便不再征询张淮深等人同意,直接率兵入城,并在城外,搜查李氏、宋氏余党。
其中宋氏情况稍好些,属于两面下注,在张淮深和张淮鼎,两边都有子弟投资,涉及不算深。
交出了几个主谋的性命,就算是过关
而李氏就惨了
这个从张议潮时期开始,就以“外戚”的形式,切入到归义军集团统治核心的家族,将面临灭顶之灾。
从李明振被杀后,凉军在俘虏带路下,迅速控制李氏在城外的庄园,凡是沾边的家族子弟,成年男性,都难免一死。
当然,这种具体操作,杨师厚不会亲自去做,而是把人先拿下,绑了交给张淮深。
也算是对方应当给的,某种“投名状”
张淮深不傻,当然知晓自己现在的处境。
人家不远千里,兴师而来,当然不可能是为了做慈善,自己必须要尽可能,在以凉王为主导的秩序中,给张氏,谋求一个有利位置。
起码不能比灵州韩氏之类差吧
于是乎,整个敦煌李氏,凡十二岁以上男丁,达数百人,血流成河,斩杀殆尽,其余妇孺,也大都作为战利品,分赐给守城立功将士。
这个在敦煌扎根数百年的汉家豪族,因此灰飞烟灭,彻底淹没于历史洪流当中。
张淮深把李氏连根拔起后,也是相当识相的,把敦煌城防交给了杨师厚,自己带着仅剩的两千多归义军士卒,驻扎于城南。
对于这样的表态,其实军中也有些怨言,觉得张淮深是否过于软弱,就这样把沙州拱手相让。虽说此战,的确是凉军出了大力,但人总是这样,记仇不记恩,归义军将校,大都是本地汉家豪族出身,一向是瓜沙地区的土豪,哪里又轻易愿意,屈居人下?
但这些意见,都被张淮深压制了下去。
张淮深自幼跟随张议潮,在西北闯荡,还是很明白道理的。
他知道,瓜沙这个地方,本来就不是什么能够争霸天下的龙兴之地,甚至连割据都够呛,过去几十年,无非是仗着中原朝廷,战乱不断,无暇西顾。西域这边,又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强大政权,才能在河西走廊夹缝中勉强维持。
现在凉王意图开拓西域的野心,显而易见,与其螳臂当车,变成完全的牺牲品,还不如就此,把宝押到凉王身上,给张氏求一个从龙之功。
虽说从时间上,张氏归附比较晚,但归义军毕竟还是家底雄厚,以此投靠,张氏未来不难在新兴政权中,得到一个有利位置。
杨师厚一开始还颇为防范对方,但见张淮深如此豁达,便也不再干涉。
十五日之后,凉王仪仗终于抵达敦煌
杨师厚、张淮深,率城中一并文武官吏,军中将校,出城二十里迎接。
张淮深率先一步,直接朝着凉王车驾,大礼参拜,表示自己治家不严,以至于祸起萧墙,感谢凉王出兵平乱,自己作为归义军节度使,理应向河西经略述职,并以治军不严的罪名,自请向朝廷辞去归义军节度一职。
这当然是一种姿态,表明归义军愿意完全听从李业处分。
李业当然不会真的让张淮深辞职,相反,连忙下了车驾,把对方扶起,再三安慰。
言道
“归义军乃张太保功业遗泽,本王岂敢擅专?还请尚书放心,日后仍以公领归义军节度如旧,归义之号,业绝不会轻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