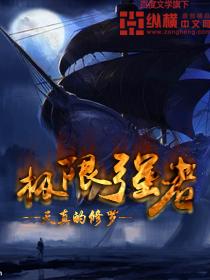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郭沫若代表作诗集有哪些 > 第29章(第1页)
第29章(第1页)
1作者原注:圣母玛利亚之名号。
2作者原注:情书。
自分是已经死了的人却睡在安软的床上,又是一场梦境吗?瑞华坐在床头执着我的两手,模糊间有许多穿白衣的人,我知道是睡在病院里了。我口苦得难耐,我要些茶水,声气好象不是我自己的声音。瑞华把些甜汁来倾在我的口里,大约是葡萄酒的光景。瑞华的眼里我看见有一种慰悦的光辉。我冷得不能忍耐。白衣人们都很欢喜的样子,有一个人对瑞华吩咐了些什么,都先后退出去了。黄色的电灯,好象在做梦的光景。
我是在昨晚上被h村的渔船救起的,当时抬到这大学病院里来,直到现在,人事才清醒了。已经夜半过后了。儿和女听说是托了s夫人。
我冷了一会又发起烧来,模糊之间又不省人事了。烧退时是第二天的中午时分。医师说只要没有并发的症候,再将养两个礼拜便可以望好。
第二天午后瑞华去把儿女引了来,病室里有两张寝台,一家人便同住在这里。晚上最后的检温时间过了,儿女们都在别一张寝台上睡熟了。瑞华坐在床缘,我握着她的手只是流泪。
她问我:&ldo;你为什么要这样伤心呢?你是因为不能毕业吗?……这一学期不能毕业,到来一学期不过迟得五个月的光景,没有什么伤心的必要呢。&rdo;
我哭着只是摇头。
‐‐&ldo;你怕你跳水的事情传出去不好听吗?这是你近来神经衰弱了的缘故,这是病的发作呢。我恨我平时没有十分体贴你,使你病苦到这步田地。&rdo;
我愈见哭,只是摇头。
‐‐&ldo;别只是伤心罢,烧才退了,医生还怕有别的并发症呢。你是怕有并发症吗?&rdo;
我到这时候才哭着把去年春假以来的经过,详细告诉了她。她静默着听到最后,在我的额上亲了一吻。她说她很感谢我,能把这一切话都告诉了她。她又说开始是她的错误,她不该说她的眼睛好,睫毛好。最后说到毕业的事情,她叫我不要心焦,只要身体好起来,迟五个月毕业也不要紧。她这些话把我的精神振作了起来,我也没有什么并发症,比医师所预料的早一个礼拜便退了病院。以后我到九月毕了业,毕了业便直接回到上海,在上海直住到今年的正月。那段时期的生活你是晓得的呢。就是我自己也觉得我对于donnacarla几乎是全然忘记了。
啊,我恨死那跛脚的s夫人!她就好象那《acbeth》中的妖婆一样,我的运命是她在播弄着的。donnacarla的住处,是她告诉了瑞华,我才知道。回国以后,她在今年正月写了一封信来报告我们:说是donnacarla在f市做了咖啡店的侍女!啊,啊,看看已经愈合了的心伤,被她这一笔便又替我凿破了!我对于她的同情,比以前更强烈地苏活了转来,我对于她的一年间的健忘,残酷地复起仇来,我又失掉了睡眠,失掉了我的一切精力。朋友,你大约还记得罢?我自从正月以来吃过你多少溴化钾,你大约还记得罢?
咖啡店的侍女‐‐这在上海的西洋人的咖啡店中是有的‐‐在日本是遍地皆是。咖啡店的主人为招揽生意计,大概要选择些好看的女子来做看板,入时的装束,白色的爱布笼1,玉手殷勤,替客人献酒。这是一种新式的卖笑生活‐‐我的donnacarla终竟陷到这样的生活里了。我为要来看她,所以借口实习,在四月里又才跑到了这里来。‐‐朋友,请恕我对于你你们的这场欺骗罢!‐‐我初来的时候,向s夫人问了她的咖啡店,我走去探问她时,她已经在两礼拜前辞职了。我的命真是不好。我以后便在f市中成了一个咖啡店的巡礼者。f市的每家咖啡店我都走遍了。我就好象去年东京地震,把儿女遗失了的父母在各处死尸堆中拨寻儿女的尸首一样,我在这f市咖啡店的侍女中拨寻我的donnacarla。这两个月的巡礼把我所有的生活费都用尽了。我前天跑到s夫人那里去向她借钱,她把她的一对金镯借给了我,叫我拿去当。她的丈夫又往外县去视察去了。她留我吃晚饭,备了酒,十分殷勤地接待着我。
1作者原注:英文apron的音译,从胸部一直垂下的长围腰。
这位s夫人是这h村上有名的美人,和我是上下年纪,只是左脚有点残疾。她是因为这残疾的缘故呢,或者还是因为自尊的缘故,我们不得而知,她是素少交际的,和她往来的日本人几乎没有一个。她的丈夫是一位法学士,在这下县的县衙门里做事情。他们没有儿女。他们连和县衙门里的同僚们都没有交际,但是奇怪的是他们和我们非常要好,尤其是s夫人,她对于我有些奇怪的举止。
她留我在她家里吃酒,她亲自替我斟,有时她又把我喝残了的半杯酒拿去喝了。她说她年轻的时候住家和&ldo;游廓&rdo;1相近。娼家唱的歌她大概都记得。说到高兴处,她又低声地唱起来。就在这个状态之下我向她借钱,她把羊上的金镯脱给了我的。
1作者原注,日本的娼楼。
我近来酒量很有进步了。在咖啡店里日日和酒色为邻,我想麻痹我的神经。我醉了,忘记了瑞华,忘记了我的儿女,也也忘记了她,忘记了她的眼睛,我最是幸福。醒来便太苦了,我是在十字架上受着磔刑。
我在s夫人家饮了四合酒的光景,醉了。我要走,她牵着我的手不许走:
‐‐&ldo;外边在下雨,你也醉了,今晚上就在这儿睡罢。&rdo;
我听她把我扶到一只睡椅上睡下。她收拾了房间,把大门掩上,打了一盆水来替我洗了脸,她自己也洗了。她把衣服脱了,只剩下一条粉红的腰围,对着镜子化起妆来。她是背着我跪在草席上的。粉的香气一阵阵吹来,甜得有些刺心。她的头发很浓很黑,她的两肩就好象剥了壳的一个煮熟了的鸡蛋。她的美是日本人所说的一种娼妓美,鸡蛋脸,单肩,颓唐的病色‐‐从白粉下现出一种青味,颜面神经要一分也不许矜持。她一面傅着粉,一面侧转头来看我。她问我:她比我的donnacarla怎样?我装着醉没有答应她。她装饰好了,起身铺起睡褥来,被条是朱红缎面的新被,她说这缎面便是我们送她的,今晚上才盖第一次。她走来看我,又走去衔了几粒仁丹来渡在我的口里,我微微点着头向她表示谢意‐‐但是我的心里实在害怕起来,我在筹划今晚上怎样才可以逃脱她的虎口。她坐在睡椅下,把两脚伸长,把右手的上膊擎在我的胸上,她的脸紧紧对着我。她说我那样迷着donnacarla,她不心服。carla就只一对眼睛好,但是没有爱娇。她最后说她才不久看见carla梳着&ldo;丸髻&rdo;1了。她说她往车站上去送朋友的时候,看见她和一位商人风的肥黑的大汉坐在二等车里,她的老祖母在车站上送行。车要开的时候,她的老祖母对她说:&ldo;到了东京,快写一封信回来。……&rdo;我听她说着这些话,心里就象有尖刀刺着的一样。她还说怕她是成了那位商人风的大黑汉的外妾了。‐‐啊,妖婆哟!你要把我苦到怎样的地步呢?但我在装着醉,我尽她说,尽她殷勤我,我一点也没有发作,我知道她是在燃着了,她抱着我,她说她怎么爱我,在心里想了我四年。她叫我脱了衣裳去睡。我一点声息也不作,一动也不动,只是如象死人一样。她揉动我,催促我,看我不应,她又把冷水来冰我的额头,把仁丹来渡在我的口里,我只把口张着,连仁丹也不咽一下。她窘着了,什么方法都用尽,而我只是不动,她最后把了一条毛毯盖在我的身上,她好象失望了的光景,她独自去睡了。……睡了一会,她又起来,又来作弄我,她最后在我大腿上扭了一把,叹息了一声,便把电灯灭了。我在心中不禁暗暗发起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