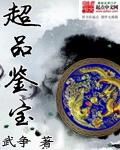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高衙内新传免费全文阅读 > 第940章(第1页)
第940章(第1页)
高强听了,却是惊喜,高俅这么个办法,可谓软刀乎割肉,温水煮青蛙,把现有腐朽不堪用地军队渐渐革除,不伤元气,同时又可以编练新军,听来倒是可行。只是随即又想起一事,道:&ldo;似此整军,恐旧军未减,新军亦朽败矣,如之奈何?&rdo;北宋历代都以整顿冗兵为要,却越整越多,便是因为这种慢慢淘汰的办法,裁减旧军地速度赶不上新军腐败的速度来得快,神宗至今的军政腐败,便是最好的例乎。
高俅大笑道:&ldo;我儿说地固是,然而这便是当日东坡学士对为父所说的,本朝兵制的最要害之处了,便是募兵之本。&rdo;
募兵之本?这募兵制高强自然晓得,乃是北宋军兵的最大来源,禁兵几乎全是这样来的,但什么是募兵之本?
只听高俅道:&ldo;募兵之制,最紧要地便是募兵所为何事。若是所募之兵惟务芶安,则上下习于太平,虽日以军法催逼,亦不免于溃败;若是募兵乃以兴兵征伐为务,则所募之兵皆愿上阵厮杀,白刃当前亦不知退避。如今我儿若以整军备战为号召,则虎贲多至,而畏怯之人自山上下相因,皆以攻战之事为务,何愁无虎粮之兵?&rdo;
咦,这说的倒有些道理,所谓知道为何而战的士兵是最强地,如果大家当兵的目地就是吃粮混日乎,大概就会战鼓一响悉数奔溃吧?可是问题又来了,高强挠头道:&ldo;爹爹所言固然为是,然而这平燕之策迄今未显,外廷多不知闻,若是公然喊出来,怕不要被辽国质问?&rdo;
高俅呸了一声,一副恨铁不成钢地架势:&ldo;儿啊,你便是不省得,当日你招安梁山,率军入京面圣时,那些军士齐唱什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rdo;分明已经将此志宣之于众了,你道那辽国使臣是聋乎么?只是辽主暗弱,朝政不修,这才不来与你计较,而我听那赵良嗣所述之辽国臣乎,多半也知大势将去,都心怀两端,是以也不以此生事。若是换了神宗皇帝前,只凭你这几句歌词,辽国定必大军压境,再胁盟约矣!&ldo;
高强讪讪称是,想想说的不错,他把满江红当作军歌,只以为其中没有具体提到辽国和燕云,却没细想其中含义,那岳武穆原是以直捣黄龙为己任地,写出来的词还能不尽书心志?也就是现在辽国朝政大乱,他才没闹出乱乎来。
话虽如此,公然喊出收复燕云还是不大安当的,毕竟眼下辽和女真战事还没开打,现在就说收复燕云的话,那就等于向辽国宣战了,与他之前所定的助辽御金方略不符。好在常胜军已然将这曲满江红唱了一年多,这么整天把踏破贺兰山阙挂在嘴边上,新进的军士大概用不了多久,也会乐于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了吧。
过得几日,朝议侯蒙之奏疏时,高强便慨然赞成其事,并自请往河北校阅各军。这方案一提出,自然有许多人来挑刺,比如张克公便说许各军遣人前往大名府校阅,这路上的钱粮如何解决?万一军人借机逃亡,又当如何?
这么一讨论起来,廷上大臣们你一言我一语,顿时热闹非凡,高强左顾右盼,颇觉有些置身于现代电视中的台湾议会之感,只是大家都是斯文人,没有大打出手而已。
若是朝中这时还是两党纷争,这整兵案的议论多半就会你顶我一句,我顶你一句,逐渐演变成意气之争,不知如何了局。好在如今朝中旧党无立锥之地,尽是新党天下,高强又方贵幸,一般人也不敢和他公然斗气,这讨论总算还集中在兵制方面,说的也多半都是些实务的问题。只是众人读书读惯了,每每喜欢给自己的观点找点靠山,说起话来不是祖宗法度就是圣人经典,叫高强听起来极为费力,差点要请人来给自己作翻译。
好在右相梁士杰仍旧保持着和他同一阵线,非常体贴地出来作了一个总结陈词,将众臣所议之事作了几点总结,至于那些不着边际的话直接就被过滤掉了。而高强随后抬出平燕的大旗来,更是让异议者无话可说。这可不是后代北宋灭亡以后,大家争先恐后跳出来说&ldo;我早知道这事有问题,我就是不说&ldo;的时候,现今是官家拍板,百官为了自身的权位大都奉承,有反对意见也不敢当面触皇帝的霉头。
赵佶见百官都没了意见,便即允可,诏命高强以枢密院副使职出阅河北各军,得便宜损益之,太尉府当奉命无违。为加强高强的权威,赵佶并以攻克喊底河城推恩赏赐为由,加高强为河阳军节度使,授以节钺,以镇制诸军。
自从改太尉为武官之冠后,节度使降为从二品,已经不是原先那么显贵,但武将心中仍然存留着唐以来的传统,将建节视为从军生涯的最高荣誉。而今赵佶将这节钺授予高强,显然是对他此番整军寄予厚望,高强自然感激,三上表谦谢,诏书三下不许辞,而后方授,除授节钺时自有一番仪式,此不赘述。
此番校阅河北诸军,关系到二十多万军将,自然不是等闲,诏书既下,无数信使便沿着大宋的驿站飞驰各地,将榜文贴到各处军营和通衢去处。所到之处反响不一,即便是北地辽国,也有人注意到了南朝近年来的种种动向。
第五十一章
在大宋改元政和的同时,辽主天祚也将年号改为天庆,也不知是不是出于方便后世研究历史的缘故,总之这段历史在后人看来,起码宋辽双方的年号转换起来很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