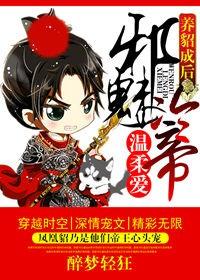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鲁迅评传吴俊 > 第74章(第1页)
第74章(第1页)
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39;宣传&39;就是。美国的辛克莱说一切文艺是宣传。&39;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
相信辛克莱的话
家又说他是&39;浅薄的社会主义者&39;。但我也浅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
以的。但我
、,;
脾
鲁
迅评传
,不必忙于挂招牌。&39;稻香村6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6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也并不比6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39;技巧,,革命文学家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
,
,、≈-乂
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ot;1这话就说得很明白了,政治宣传可以用文艺为工具,但文艺并非一定要成为政治的工具,而宣传文字,又不一定是文艺。所以我们说鲁迅是自由主义者,一点也不带附会的成分的。
他在那回讲演中还有一段深刻的话:&ot;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ot;&ot;革命成功以后……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
非被排轧出去不可。&ot;2这话说得太明白了,要歪曲也不可能的呢!
迅的文章,有时候要因时因地因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他对于
革命&ot;并不觉得怎样乐观的(这道理,上文巳经说过、对于革命文学,也不觉得有多大的意义的(事后,要替他附会起来,好似他早就是辈命文学的前驱,也可不必。他对于文学的作用,也并不十分看重的〉。他从北京南下,在厦门住了半年,又在革命策源地的广州住了九个月,对于所谓&ot;革命&ot;与&ot;革命文学&ot;,更看得透了。
一【十五文艺观
此,鲁迅替&ot;革命&ot;与&ot;革命文学&ot;书出了这么两幅图画:他说:&ot;欢喜维持文艺的人们,每在革命地方,便爱说&39;文艺是革命的先驱,。我觉得这很可
或许外国是如此的罢;中国自有其特别国情,应该在例外。现在妄加编排,以质同志(一)革命军。先要有军,才能革命,凡已经革命的地方,都是军队先到的:这是先驱。大军官们或许到得迟一点,但自然也是先驱,无须多说(这之前,有时恐怕也有青年潜入宣传,工人起来暗助,但这些人们大抵已经死掉,或则无从查考了,置之不论)。(二)人民代表。军官们一到,便
有人民代表群众集车站欢迎,手执国旗,嘴喊口号:&39;革命空气,非常浓厚,这
1《鲁迅全集》第4卷,第94一95页《鲁迅全集》第7卷,第476页。
鲁迅评,
是第二先驱。(三)文学家。于是什么革命文学,民众文学,同情文学,飞腾
文学都出来了,伟大光明的名称的期刊也出来了,来指导青年的:这是
可惜得很,但也不要紧第三先驱。外国是革命军兴以前,就有被迫出国
的卢梭,流放极边的珂罗连珂。&ot;1这当然是讽刺文学,然而使我体会到他所见的国民革命,正是辛亥革命的翻版,&ot;走狗教不会新把戏&ot;的。
而&ot;革命文学&ot;这一概念的模糊,他看了觉得十分可笑。他会举了如次的
事实:&ot;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意大利的唐南遮,德国的霍普德曼,西班牙的伊本纳兹,中国的
吴稚晖。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逆,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都应该做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39;打打,、&39;杀杀&39;或&39;血血,的。如果这是&39;革命文学&39;,则做&39;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幵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于无&39;杀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39;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39;革命文学、从喷泉出来的即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39;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ot;2他的文章,经过许多岁月,还是值得重看一回的。
鲁迅对于当时的&ot;革命文学&ot;不作过多的期待,直到他回到上海以后,还是如此。他曾在答冬芬的信中说:&ot;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要走人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社会停滞着,
文艺决不能独自飞跃。&ot;1他是要投人现实社会去的。
时下若干现代文学史中,把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所开展文艺自由论争,作
为鲁迅所领导的方向之一。那次论争是由胡秋原所开始的;他发表了艺术
非&ot;至下&ot;论,认为:&ot;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
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ot;&ot;文化与艺术之发展,全靠各种意
见互相竞争,才有万华缭乱之趣;中国与欧洲文化,发达于自由表现的先秦
与希腊时代,而僵化于中心意识形成之时。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结果只有奴才奉命执笔而巳。&ot;接着发表了钱杏邨〈阿英)理论之清算,喊着要求文
学的自由,其中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另外,当时一位青年作家杜衡(苏
汶)他发表《关于&ot;文学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ot;》攻击&ot;左联&ot;是目前主义,只有策略,不要真理,说:&ot;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斗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