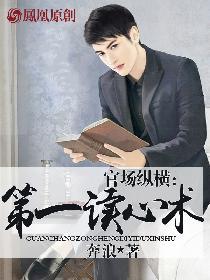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美容师学徒一般学多久 > 第5页(第1页)
第5页(第1页)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从口袋里拿了一个苹果递给她,心里惴惴不安,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小杂货店里买的蔫巴便宜苹果,被她拿来作为借口羞辱我的可能性非常之大……但是她没有如往常一样损我,而是温和地接过去,半天,问我:“你昨天在走廊上遇到孙先生了?”啊,你知道了?这个,不够刑拘十五天,或者驱逐出境吧?她对我的嘀咕一无所知,轻轻叹口气,出了半天神,老实说我对她如此漠漠轻愁的神态相当不适应,前途不晓得是吉是凶。她说:“我老公,二十年前追求我。他很爱我,经常往我家跑,和我的亲人都相处得很好。”我屏息凝听。一个故事慢慢在我面前展开画卷,一个普通的男孩子,爱上一个普通的女孩子,用一种很普通的方式爱——去讨她的欢心,她父母兄弟姐妹的欢心,把自己从一个陌生敲门人,变成了家庭的一分子。有一天,他悄悄买了机票,定了酒店,想给心爱的女孩子一个惊喜,带她和她全家的人,一起去一个美丽的地方度假,在开车赶去机场的路上,一场意外猛然降临,除了女孩和他,其他人都葬身在车祸里。他得到他所梦想过的——和女孩子结婚。在萧条的婚礼上,他说,我永远都爱你,我会照顾你直到我死,你所失去的我都要给你补偿。而新娘的誓言是,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我永远都恨你,就算你为我做牛做马,做到死我也不会多说你一句好话。当一个人的心灵被仇恨和哀伤蒙上,就如她永远生活在彻底的黑暗中,眼睛对于光明毫无感知,久而久之失去分辨是非的能力。一过二十年。甚至连理由都忘记了,甚至那痛彻心肺的记忆也在淡化,只有强大的惯性还在推动恨的前行,心上的厚壳那么硬,多么温柔细腻的爱情都无法潜入感应。她糟蹋自己,用以折磨丈夫。很成功,也很失败。这么简单,但是惊心动魄的故事。两个人整整一生的时间,用在没有目的和结果的死掐里。讲完的时候,窗外已经暮霭沉沉,我无言地看着房东太太,她眼里有泪光,闪闪烁烁,忽然惊动梦境似的一擦脸,说:“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急忙站起来,当我不存在一样,大步流星走了,在走廊里听到她大嗓门吼:“死鬼,开门!”不知为什么。我分明听到那吼声中有一丝爱恋,只不过,连当事人自己,也从来没有分辨出来过。五、善良人的世界发完呆,我伸了个懒腰准备进房,这时候才发现陈太太还没有回来,咦,这都七点了,不会那家幼儿园的活儿这么多,多到要加班吧。放下东西我跑出去,不过几分钟就到了巷口的幼儿同,远远看到门口停了一辆非常豪华的车,有钱人就是没意思,这里是慈善幼儿同好不好,名额是留给穷人的呀,你凑什么热闹。围着那辆车绕了两圈,羡慕了一下,走进去,我喊:“陈太太、陈太太。”幼儿园所有教室都锁了,只有走廊尽头一个小房间开着灯,我向那个小房间走过去,一边走一边喊:“陈太太,你在吗?”一条人影忽然从那个小房间里蹿出来,一下到了我的身后,我吓了一跳,立刻摆出虎鹤双形手,怪叫一声:“谁?”结果就是陈太太,她穿的是幼儿园里做清洁的蓝色工装,头发绑起来了,脸相清秀得要命,不过表情就难看一点儿。你遇到蟑螂还是老鼠了?那么厌恶的样子,别怕,我去帮你打。结果从小房间里慢慢走出来一个人。就算是背对灯光,昏暗中看得不清楚,我也可以担保,这个人绝对不像蟑螂或老鼠。倘若非要类比,一句俗到极点的话可以成功满足我的要求——人中龙凤。老龙凤……这个男人显然年纪不轻了,头发花白,但身形挺直,容貌清朗,一点儿疲态都没有,双眼炯炯,向我一眼看过来,简直把我五脏六腑都照了个通透。我顿时感觉自己气泄了一半多,不过陈太太的手紧紧抓住我的衣角,似乎也知道我随时可能拔腿开溜的念头,说不得,我只好强出头,喝问:“你是谁?”那人缓缓说话,不怒自威:“你又是谁?”他其实根本不想知道我是谁,转头看着陈太太:“丫丫,跟爸爸回家吧。”爸爸?我眼珠子立刻就想离家出走,我瞪着身边穿蓝色工装的陈太太,姐妹,你要不要啊,你老爹开几百万的车,你在这里赚一千块一个月?够你买轮胎印吗?陈太太理都不理我,倔强地站在我身后,好久,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没什么爸爸。”一把拉住我,“走。”说走就走,她砸钢筋也不是白砸的,那力气可真大,一拽就把我拽出去了,我向后张望,隐约感觉那男人在陈太太说话的时候,就好像给谁抽掉脊梁骨一样,顿时老得一塌糊涂,靠在门上,动也不能动。我跟着陈太太疾行,一直走到公寓楼门口,她忽然放开我,整个人扑倒在楼梯上,猝死了一样。我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半天才上去把她轻轻扶起来:“你还好吧。”她满脸是泪,犹自哽咽,几乎气都喘不过来,抓住我胳膊的手跟扳手一样硬,我说:“你要掐死我的话部位选错了,往上移十几公分,我保证马上就挂,绝无虚言。”她给我逗得忍不住一笑,慢慢静下来,坐在台阶上长出一口气,说:“那是我爸。”我猜也是,世上的怪事多了,也没见过谁无缘无故去当人家爸的。“干吗不跟他回去?”这个疑问全世界的人都会有。她摇摇头,不说话,低头不知道想什么,猛地跳起来大惊失色:“我把波波他们放幼儿园教室里了,糟糕。”撒腿就冲回去。等我们回到幼儿园的时候,原本波波他们呆的教室门大开,不要说四个活生生的小孩子,就是四条影子都没看到。在显眼的地方放了一张纸条,钢笔写着:“丫丫,孩子我接回家住几天,你随时来找他们都可以。”老头儿,这叫绑架好不好。绑架判很重的啊。你懂不懂法的?陈太太反而比我冷静得多,看我一眼:“他是法学博士出身。”说完转身就走了,我追上去:“你不去找孩子?”她一声不吭,其委顿程度,和砸完钢筋回来的样子差不多,沉默地,一步一步地挪,挪回了家,开了门,坚持到了床边,当啷一声倒下去,床架子一声哀号,眼看就要散架。我过去也不是,不过去也不是,关键是饿得要死,实在有点儿撑不住了,就算有菜青虫的面我都要吃一碗,结果悄悄溜到门口,床架子在背后又“哐当”一声,莫非终于塌了?回头一看,陈太太目露凶光,爬起来四处摸索,不晓得找什么,从嘴里喃喃的内容看,我的命运今天极为叵测,不是被害人就是从犯,两者都非我人生第一志愿,纯属调配所得,她说:“我不会放过你,我不会放过你……”终于摸索的行为有了结果——一把水果刀。在她没有办法和我直接卯上斗力以前,我狠下心从陈太太脖子上给了她一掌,多年保安生涯我也算是专业,要让一个人失去知觉又不至于受伤,多少还是有点儿经验的。把她放平,我心里祈祷现在千万不要有人进来,否则不要说跳进黄河,就是把黄河背在身上,我一辈子的清白名声也毁了。其实,我不过想给她做个脸而已。昨天房东太太做了磨砂膏的实验品,效果没有洗脸液那么突出,但是从她说话声音忽然低了数度,对房东先生又史无前例地略显温柔来看,那玩意儿的作用,似乎是弱化一个人内心的负面情绪。说到负面,没有什么比拿把水果刀跑去砍人,而且砍的是自己老爸更鲜明的例子了……省掉正式做脸的麻烦步骤,我直截了当,拿出磨砂膏往她脸上乱倒一气,搓搓搓,去死皮,去死心,搓去病态和顽疾,要是世间事可以都这么解决,警察们就可以统统转业了。等她从短暂的昏迷里苏醒,我已经做完了,不过出乎我意料,她并没有坐起来温柔地长出一口气,然后变成一个通情达理,万事不萦怀的圣人,可能钢筋砸久了她的顽固程度绝对比常人胜出无数倍,因此我措手不及之下,就眼睁睁看着她蹿出房门,直扑外面而去,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手里没有拿水果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