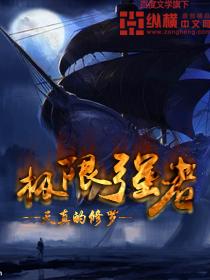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替葬重生后我被摄政王盯上全文阅读 > 第42章(第1页)
第42章(第1页)
无论是上辈子在生命最后那一刻的生死相伴,抑或是这辈子能够改变命运的唯一稻草,温浓不敢承认,但又不得不承认,她对陆涟青抱持着一种极其特殊的感情。
仰面倚躺的陆涟青忽而睁眼,吓得走神的温浓倒抽一口气:“——诈尸!!”
不对,这辈子的陆涟青是活的。
温浓捂紧嘴巴,唰一声跪地。
“诈尸?”陆涟青坐姿未变,甚至连手指都没动一下,俯身瞰她,面上的表情不似动怒,但眼底的烁光却亮得刺人:“敢情你当本王是死的吗?”
第25章蛊惑他的声音很轻,充满了蛊惑。
温浓有理说不清,差点没哭出来:“奴、奴婢绝无此意……!!”
话虽如此,可真要深究起这两个字的意思,可不正是陆涟青说的那个意思么??温浓冷汗涔涔,这事换到宫里任意一位当主子的面前说,那都是妥妥能杀头的罪。更何况眼前这位本就是出了名的脾气不好,在位摄政期间手里的人头数目简直数不胜数!
温浓吓虚脱了,忘了方才还觉得他挺慈眉善目,此刻她却仿佛已是陆涟青捏在手心的又一枚人头,好不容易重生回来,还没想好怎么活,命就搭没了呜!
陆涟青斜眼一睐,血色红光只是一闪而消,更多的意味隐在那乌色的瞳眸深底:“那你倒是说说,你是何意?”
温浓伏在地上都已经做好了人头落地的打算,闻言如聆天音,脑袋立刻弹起来:“奴婢方才是想说扎、扎实!”
陆涟青两眼一眯,凶光再露。
温浓心虚得不行,唯有硬拗:“意、意思就是说奴婢推揉按摩的功夫很扎实、有技巧,奴婢可是练过的。”
“就你那点手头功夫?”陆涟青嗤笑,显然一丁点都看不上。
温浓被嗤得脸红,顺腿而下:“那、奴婢回去再练练?”
陆涟青的笑意不明不白冷了几分:“找谁练?容从?还是容欢?”
怎么连容欢都提上了?温浓急得脑子有点转不过弯,试探着换了个:“那不然找太后娘娘?”
“近身的精细活她从来只用容从。”陆涟青毫不留情地再一次打击她:“就凭你?她还看不上。”
温浓愁眉苦思,忽然发现点题了,原来陆涟青的用意在这:“奴婢明白了,奴婢一定努力找到法子接近小陛下,留在他的身边监视他,绝不会让殿下久等的!”
陆涟青眉梢一抬,侧目看她,看得温浓有点紧张,难道她又理解错了?
“行罢。”陆涟青将眼一阖,似乎没打算继续这个话题了,“起来,本王头还在疼。”
温浓只道虚惊一场,心里大大松一口气,爬起来给陆涟青捏太阳穴。只是经此一吓心有余悸,温浓再不敢分神散漫,思及刚才提到的小皇帝,忍不住想起白露之后的那场生辰宴,她不知道是否应该提醒陆涟青。
上辈子听说信王在这场生辰宴上并无大碍呀,相反他利用这场刺杀完成了一次大肃清,并彻底实现了他的权利垄断,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敌手,直到他死去为止。
即便没有她的提醒,上辈子的陆涟青一样能够运筹帷幄,走上他的权利巅峰纵览大局,温浓只是对死在这场宴上的无辜戏子心有不忍。
她并不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可她也做不到在大事大非面前始终冷情冷静。如果没有事先接触到这些活生生的人,她可能不会顾虑太多。可人有七情六欲,一旦得到知情权,做与不做都会变成一种负罪感,温浓只是想让自己好过一点。
问题就在于,这件事应该怎么提、怎么撇清自己的关系婉转地提,很需要一番技巧。
“殿下。”温浓靠得近,声音放得很轻,挨在陆涟青耳边有些痒。他没有睁眼,懒洋洋地发出一声回应:“……嗯?”
“您若不嫌奴婢吵,奴婢给您说些有趣的段子消乏解闷可好?”温浓故作轻快。
陆涟青依旧拖着一副疲懒的状态,可有可无:“说来听听。”
“您也知道,小陛下的生辰快到了。奴婢近来时常跟随容从跑妙观斋,那里来了好些进宫献技的草班子,与宫班子差别极大,很是古怪生趣。”温浓没有夸大其辞,民班子不比宫班子风雅礼全、正儿八经,很多技艺看似粗俗,上不了台面给官家的贵人看,但私下排完戏后相互嬉闹之间,很有些逗趣的滋味,才会让温浓时常看得津津入迷。
“有的口技一流,学人学物栩栩如生;有的大腿劈到腰肢上,软得像根风蒲柳。还有一个班子唱关山狼王,头狼演得那叫一个惟妙惟肖。最后一出戏说王狼大战敌营将军,连翻十八个跟斗一跃而起,朴灰的狼皮舞天盖地,活像一只真正的巨狼!”
生怕陆涟青听不耐烦,温浓说得可劲,几乎使出浑身解数,自觉只比当说书的就差那么一点点。陆涟青没不耐烦也没喊停,不知是真在听,还是根本就在假寐休憩,对她不搭不理。
温浓说到关山狼王,故意停顿了下,一脸鬼崇又小人:“不过草班子有一点不好,就是不爱听话,还不守规矩。宫班子的人也不行,成日趾高气昂,好似他们才是主子一样。两边进宫这么多天了,天天扯皮拉架,就没一日安生过。妙观斋的黄总管头疼得不行,还说两边不和已久,就怕要在生辰宴上闹出事,影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