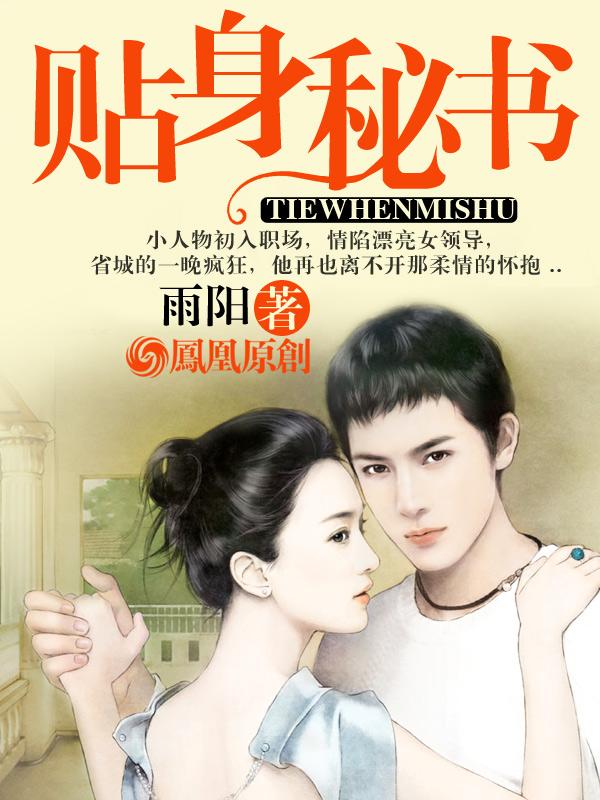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穿越狐仆×ss > 第109章 条条大路宁古塔(第1页)
第109章 条条大路宁古塔(第1页)
闵敬宗平日,也颇有些小聪明,当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现在已经是彻底的陷入了绝望。
他能怎么样呢?
他当然可以拿出证据,说清楚自己菊门的裂伤,绝对与风月无关。
可是,那又如何?
这样一来,那不是明摆着承认自己陷害同学,诬告高信之吗?
结果必然是被陈子灿乘胜追击,反坐下狱,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想想那些五大三粗,满身黑毛,凶横暴躁的荒原蛮人。
再想想自己这身细皮白肉,和娇嫩软滑的屁股,他简直连死的心都有了。
而且,即使他洗清了陈子灿强扣在他头上这无厘头的罪名,那么想想后果,不但自己遭殃,连带着家里,恐怕都不得安宁。
因为,这么做,他就得罪了齐永康。
“宁向东山斗虎狼,莫惹西城齐大郎”的齐永康。
对齐永康,他真的是又佩服又害怕。
佩服他以笔为刀,以舌做剑,杀人不见血,破财还诛心的诡谲能力。
也害怕他翻手为云覆手雨,睚眦必报,阴毒狠辣的通天手段。
坏了他的大计,恐怕将要发生的,是比死还要让人害怕的事情……
其实真正让闵敬宗更加绝望的,是另一种结局。
那就是他放弃辩解,默认了陈子灿血口喷人,强加给他的污名。
这样,就可以不得罪齐大郎。
可是,那又如何?
他既然承认了自己是个出卖男色的兔子,那么,高信之自然无罪。
因为明清立法,从来就没有强奸性工作者的罪名。
这个罪名,只适用于良家。
最终,他还是逃不了个诬告他人,反坐充军的下场。
条条大路,通向的最终目的地,都是宁古塔。
陈子灿留给他的,根本就是条死胡同,一个无解的局。
他左思右想,始终找不到出路,只能沉默不语。
杨教谕等待良久,见闵敬宗始终垂头丧气,不发一语,好像竟是默认了。
心中恨其无行,怒其不争,沉哼一声,跺了跺脚,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杨教谕走了,陈子服知道,这一局弟弟完胜。
对方已经溃不成军。
他现在就可以宣判结果,然后等弟弟出第二招。